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2008年第03期 > 中国财政2008年第03期文章 > 正文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2008年第03期 > 中国财政2008年第03期文章 > 正文走出“层级财政”
时间:2020-04-14 作者:刘尚希
[大]
[中]
[小]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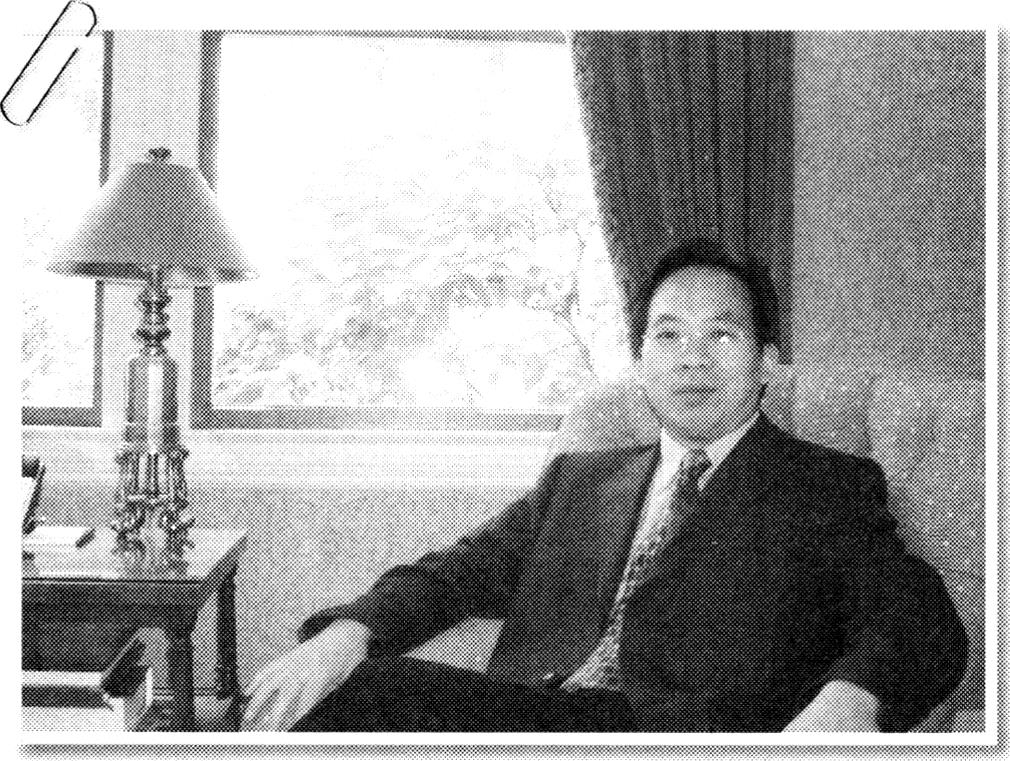
我们思考任何问题都依赖于特定的概念,离开了这些概念,我们的思维就会中断。任何知识都是建立在一系列概念基础之上的,财政领域也不例外。对一些新问题的探讨,也就是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过程,往往依赖于新概念的提出。更新知识和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更新概念,按照新概念的新内涵去理解我们原来认识的事务,从而得到一种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如果与现实过程相吻合,就能给我们的实践带来新的操作空间。
对财政的认识,实际上是在不断变化的。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财政的理解就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例如从“建设财政”到“经营性财政”,再到“公共财政”,随着这些新概念的提出,财政的运行机制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正处于重塑过程之中。“公共财政”的提出使我们对财政的整体认识与计划经济下完全不同了,从根本上变革了财政与市场的关系、财政与民众的关系,从而使财政实践、财政运行更适应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同时也使财政更符合社会公众的要求。这种变化自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以及与政府职能作用的重新定位紧密相联的。
但相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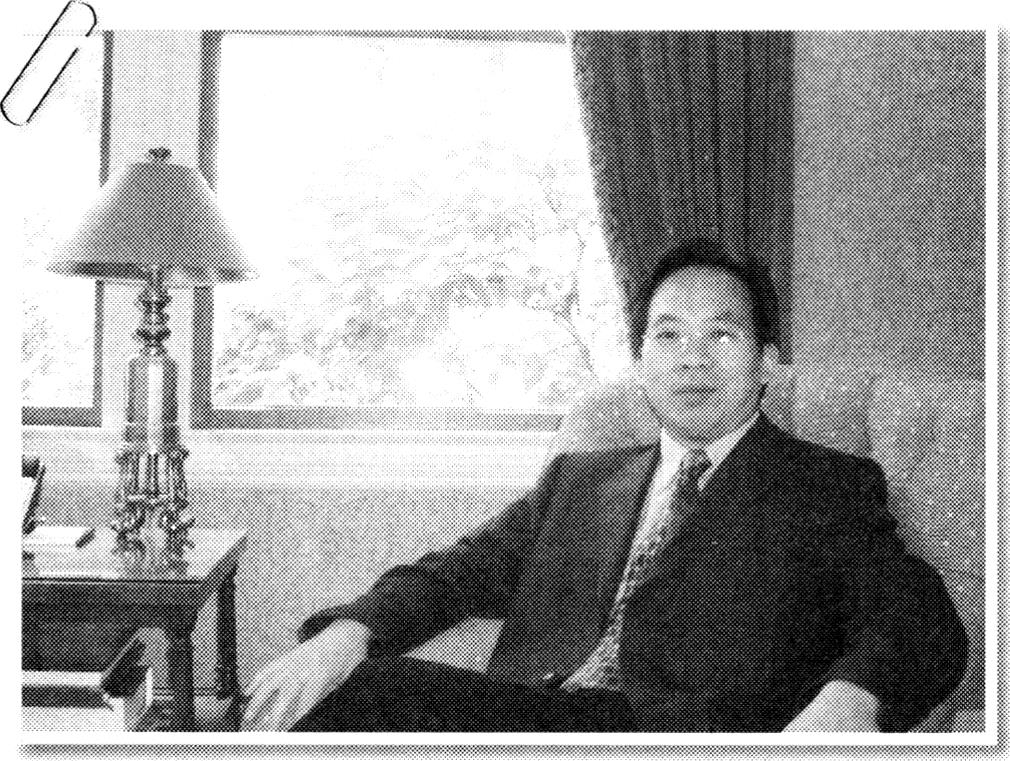
我们思考任何问题都依赖于特定的概念,离开了这些概念,我们的思维就会中断。任何知识都是建立在一系列概念基础之上的,财政领域也不例外。对一些新问题的探讨,也就是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过程,往往依赖于新概念的提出。更新知识和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更新概念,按照新概念的新内涵去理解我们原来认识的事务,从而得到一种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如果与现实过程相吻合,就能给我们的实践带来新的操作空间。
对财政的认识,实际上是在不断变化的。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财政的理解就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例如从“建设财政”到“经营性财政”,再到“公共财政”,随着这些新概念的提出,财政的运行机制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正处于重塑过程之中。“公共财政”的提出使我们对财政的整体认识与计划经济下完全不同了,从根本上变革了财政与市场的关系、财政与民众的关系,从而使财政实践、财政运行更适应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同时也使财政更符合社会公众的要求。这种变化自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以及与政府职能作用的重新定位紧密相联的。
但相比之下,对政府财政内部架构的认识却显得停滞不前,尤其是在纵向的财政关系方面,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财政体制问题,或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我们的认识并没有随着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而有突破性的进展,其认识基本上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政府间财力的分配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认识——“分灶吃饭”的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并深深地根植于当前的理论思维和实际决策之中。
“分灶吃饭”的基本内涵是,各级政府必须自己找饭吃,当时的基本表述叫做“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其实,“分灶吃饭”也就是“分级吃饭”,强调的是各级政府财政各过各的日子。究其实质,这属于笔者称之为“层级财政”的范畴,亦即通过财政的层级化来明晰各级政府的财政利益,从而调动各级政府的财政积极性。从理论上看,“层级财政”无疑地属于分权的财政,带有财政联邦主义的色彩,但由于无层级之间的协调机制,从而丧失了各层级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分权”变成了公共部门内部的“分家”。具体来分析,现行的“层级财政”有如下鲜明特征:
其一是以本级财政利益为中心。每一级财政都要自己找饭吃,这就给每一级政府带来了财政增收的压力,迫使各级政府重视本级收入的增长。这种层级财政利益的明晰化,自然形成了各级政府都以本级财政利益为中心的财政运行机制,上下级之间相互博弈,相互提防,相互“挤挖”,并以此来改善本级的财政状况。这样一来,也形成了当今愈演愈烈的上下级之间财政关系上的互不信任。与西方不同的是,这种上下级之间的博弈纯粹是在公共部门内部,与其辖区内的社会压力无直接关系。
其二是以本级财政预算平衡为目标。如果本级财政难以平衡预算,除了壮大本级财源之外,对于上一级政府而言,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那就是调整收入划分。在分税制之前,通常的做法是调整企业的隶属关系,上收盈利企业,下放亏损企业,从而达到增加本级财源和财力的目的。实行分税制之后,通常是通过税种划分来实现,如把一些大的税种留给本级,而把一些小税种划给下级。在这种调整机制下,下级财政自然处于被动、不利的境地,但这不是因为上级自私自利,而是实行“层级财政”的必然结果。
其三是以“本级经济”为基础,包括本级的财源、税源、资源和资产以及本级的各类产权。财政要增收,自然离不开发展经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提出了财源建设的理论观点。在这种理论观点的推动下,许多地方掀起了财源建设的热潮。所谓财源建设,就是从本级财政增收的角度来发展经济。凡是有利于本级财政增收的就大力发展;否则,就不发展或不热心推动发展。在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情况下,各级政府争相发展本级企业,扩大本级企业的数量和壮大本级企业的规模,尤其对那些能带来大量税收的行业如烟、酒等都是大力扶持。这种财源建设的热潮一直延续到分税制改革。直到现在,这种状况并无大的改变,变了的只是其具体的做法。当前提倡的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以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强调发展区别于省和市一级的“县本级”经济。
与高度集中的“一灶吃饭”相比,1980年开始实施的“分灶吃饭”,其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分散了国家财政压力和风险,减少了下级对上级的财政依赖,由此调动了每一级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在理财、发展经济方面的自主性大大增强,对地方各级政府而言,这种效应是十分显著的。在全面短缺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这种增收积极性无疑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尽管财政包干制限制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收入增量主要留给了地方,在中央支出仍延续原有格局的情况下,导致中央财政越来越困难,曾经一度向地方借钱过日子,但总体上看,在当时条件下,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是改变了“分钱”的办法,从按照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收入变为依据税种来划分收入。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大大缓解了区域之间的相互割据和彼此封锁的状况,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同时也改善了中央财政调控乏力的局面。就此而言,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分级吃饭”的格局并未因此而有实质性改变。从现象上看,1994年以前,中央财政困难,地方日子相对好过;之后,中央财政相对好过,县乡财政多数陷入困境。对于这种截然相反的变化,我们会很自然地归因于财政体制的改革,甚至会“归罪于”分税制财政体制。但若是深一层观察,根源仍是“老病灶”,是“分级吃饭”的必然结果。1994年改革时,我们看到的问题仅仅是当时“分灶吃饭”体制中的部分问题——按照企业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把中央财政给“包死”了,而没有意识到整个“分灶吃饭”体制的核心问题——财政层级化,只对本级财政负责。从“分级吃饭”的角度来看,现行的分税制体制与之前的财政大包干体制仅仅有形式上的不同,而无实质性的区别,都属于“层级财政”类型。
前面所述的三个特征,现行财政体制依然具备:以本级财政利益为中心,以本级预算平衡为目标,高度关注发展本级财源或税源,哪一级财政困难,就强调发展那一级经济;而改变了的只是其方式:财源建设的方式变了(从通过发展本级企业来壮大本级财源,变为通过发展与本级税种密切关联的行业来壮大本级财源),分钱的方式变了(从通过划分企业来分钱变为通过划分税种来分钱),当然结果也变了(从中央财政困难变成了基层财政困难)。现在,“层级财政”的这种负面效用越来越明显。随着全面短缺变为相对过剩,以及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压力不断增大,各级财政必须主要依靠自己找饭吃,围绕本级财政增收而去不停地开发、发展,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层层过于注重本级财政,下级财政的境况将会如何?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生态、环境危机以及县乡财政的普遍困难与此有内在关联。虽然现在不再提“分灶吃饭”,也不再搞财政包干制了,可那种层层包干,分级吃饭,各过各的日子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各级财政自求平衡的结果,必然是从中央到乡镇,迫使每一级政府都以经济增长——当然是有利于本级财政增收的经济增长——为中心,从而加剧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资源、环境的破坏,而且使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地方陷入了“越穷越开发,越是开发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可以说,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依然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分灶吃饭”基础之上,以至于学术界针对现行体制提出的一些改革思路也没有摆脱它的束缚。我们对财政体制的思考,尽管加上了更多的国际色彩,比如更多地用“财政分权”这样的概念来刻画现行体制,但骨子里的东西依然是“分灶吃饭”或者“分级吃饭”的层级财政思维,如一度十分流行的作为分税制体制最高原则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实际上就是这种层级财政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惯性使我们难以摆脱原有的一级一级地分开来考虑纵向财政关系的思维路径,很容易落入“循环改革”的陷阱而不知。因此,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首要的任务是转换思维和更新观念,从“层级财政”的框框中走出来,建立起不仅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要求,也与我国当前单一制国家架构更吻合的“辖区财政”。至于如何建立,将另著文讨论。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 方震海
 附件下载:
附件下载:相关推荐
-
无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邮编:100036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40014 投诉举报电话:010-88227120
京ICP备1904795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投约稿系统升级改造公告
各位用户:
为带给您更好使用体验,近期我们将对投约稿系统进行整体升级改造,在此期间投约稿系统暂停访问,您可直接投至编辑部如下邮箱。
中国财政:csf187@263.net,联系电话:010-88227058
财务与会计:cwykj187@126.com,联系电话:010-88227071
财务研究:cwyj187@126.com,联系电话:010-88227072
技术服务电话:010-88227120
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财政杂志社
2023年11月
-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 投诉举报电话:010-88227120
- 邮编:100036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