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2014年第20期 > 中国财政2014年第20期文章 > 正文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2014年第20期 > 中国财政2014年第20期文章 > 正文优化公共安全财政支出保障机制的思考
时间:2020-02-12 作者:张洪波 (作者单位:江苏警官学院)
[大]
[中]
[小]
摘要:
目前,我国公共安全经费预算与支出整体上随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不断攀升,支出的效率基本得到政府和民众的认可,但是面对居高不下的公共安全整体费用、日益严峻的危机和风险挑战,公共安全的支出结构还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公共安全支出缺口较大,人均供给较低,安全前景不容乐观。我国公共安全支出的总量虽然较高,但是人均后依旧处于世界较低水平,整体缺口较大。国际上通常采用两项重要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公共安全能力,即国家财政供养的维护公共安全人员数量和公共安全财政支出。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最新估算,全世界各国每10万人口占有警察人数平均约为300人,只有不到10个国家的每10万人口警力数低于100人。截至2014年,按照全国财政供养的160万正式警力计算,我国每10万人口平均警力已经增至120人,但仍然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1990年到2003年,我国警察编制仅增长十余万,而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最剧烈的一个阶段。2004年以后,这一数字虽然出现一个明显上升,但主要原因在于将先前的地方编制转化为国家编制,实际在编人员数量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而在同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警察力量普遍得到增强。例如2001年至2010年,英国警力增幅15%,...
目前,我国公共安全经费预算与支出整体上随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不断攀升,支出的效率基本得到政府和民众的认可,但是面对居高不下的公共安全整体费用、日益严峻的危机和风险挑战,公共安全的支出结构还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公共安全支出缺口较大,人均供给较低,安全前景不容乐观。我国公共安全支出的总量虽然较高,但是人均后依旧处于世界较低水平,整体缺口较大。国际上通常采用两项重要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公共安全能力,即国家财政供养的维护公共安全人员数量和公共安全财政支出。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最新估算,全世界各国每10万人口占有警察人数平均约为300人,只有不到10个国家的每10万人口警力数低于100人。截至2014年,按照全国财政供养的160万正式警力计算,我国每10万人口平均警力已经增至120人,但仍然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1990年到2003年,我国警察编制仅增长十余万,而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最剧烈的一个阶段。2004年以后,这一数字虽然出现一个明显上升,但主要原因在于将先前的地方编制转化为国家编制,实际在编人员数量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而在同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警察力量普遍得到增强。例如2001年至2010年,英国警力增幅15%,在美国50个最大地方警察机构中,有10个机构的警力规模呈现两位数增长趋势。公共安全的财政支出是衡量国家维护公共安全能力的另一项指标。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国警察经费投入主要以人事的高度集权和财政的高度分权为基本制度安排。近十年来,公共安全财政投入增长幅度一直低于同期财政增长幅度,与城市化进程及快速上升的公共安全需求并不匹配。以大都市为例,相关调查表明我国重要大都市的公安财政投入规模与全国各省财政投入平均水平差别不大,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区别明显,如美国主要大都市(除洛杉矶外)在2011年财政支出全部超过上年20%以上,公共安全的财政支出普遍逐年增长。
其次,公共安全支出细化不够,尚不能满足支出信息公开的需求。目前中央一级的预算公开中,由于涉及的金额庞大,也仅仅做了一些粗略的细化。根据财政部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的《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12年国防预算为6702.74亿元,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7017.63亿元,此处的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也包括加强基层监管部门食品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促进保障食品安全所涉及的投入。该数字并不属于精确意义上的公共安全,所以为了避免混淆,财政部公布的2013年中央财政预算中将公共安全预算数修订为1289.89亿元,比2012年执行数增加106.43亿元,增长9%。从目前财政支出信息公开来看,还不足以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再次,公共安全支出扩张越位,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中央和地方在公共安全的具体事权和财权分配上尚有分歧,从而造成阶段性、地域性的安全供给失衡。从供给业务来看,私人侦探、监所等业务尚没有对私营企业开放,保安、特勤等业务尽管已经从公安业务部门脱钩,但是行政许可和日常监管的压力和成本依旧较大,一些本应该由财政负担的安全项目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实际上,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来激励私营企业提供公共安全,或者通过管制要求企业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安全并承担成本。以美国为例,在2001年“9·11”事件后,国会和布什政府重新审视了航空安全问题,最后国会决定支持政府直接提供安全服务,并通过了《航空及运输安全法案》,成立了交通安全管理局,由交通安全管理局担负起雇用检查人监控机场中所有检查站的责任,而由航空公司承担安检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发达国家在公共安全支出领域也曾面临着与我国当下类似的窘境,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新兴福利国家的问题日益显现,不断增加的国家服务机构、收入分配转移和所承担的责任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财政问题,尤其是协调和控制问题。最终人们达成了新的共识,认为老一套的国家机构缺乏足够的准备和完善的设施,应通过不断地改革创新,逐渐建立起相对平衡、充分的公共安全财政保障制度。德国在这一领域成绩尤为显著,堪为表率。
德国是由16个联邦州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实行联邦、州、地方三级行政管理,公共安全(治安)属于州、地方的事务权限。1992年,德国国内公共安全财政开支达到了229亿马克,1996年猛增到274亿马克,并且每年都在持续增长,而德国的整体财政状况并不理想,预算的限制让警务部门的效能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减少支出,提高效率,德国警务开始了新公共管理改革,改革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领导体制、组织框架同私营部门相类似,比如管理预算、绩效合同、目标管理等。二是目的导向的行为模式,比如产出计算、质量管理。三是通过引入竞争和顾客导向的运行机制来激活这些新的结构和工具,比如基准测试、市场测试、合同外包。通过将公共安全等任务管理化、合同化、外包化和市场化,德国实现了公共安全供给机构的精简和瘦身目标。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不是国家或地方政客,而是地方行政管理者,相较于通过简单的私有化和加强并改革公共服务部门以促其精简,这种新的主导理念被视作良好的替代方案,因此获得了各个党派的广泛支持。改革确实适度减少了开支,德国2004年的国内公共安全开支为324亿马克,增幅只有1992年到1996年阶段的一半。
面对公共安全支出上存在的三点问题,结合德国的经验,我国在公共安全支出上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予以调整和优化。
第一,针对公共安全支出的总量缺口,合理配置公共安全的人事权和财权。作为地方性公共产品,公共安全的支出应该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同时合理区别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比例。美国联邦政府运用多种方式对州政府财政和地方政府财政施加影响,利用一些专用拨款项目将税收款项回流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如社区警务服务办公室(下辖于司法部的部门之一)的项目和国家安全局设立的项目。我国的人事编制高度集中于中央和省级政府,但是地方同样享有很大的财政权力,这种矛盾导致地方只能大量聘用可以带来维护公共安全却无法给予编制的辅警。目前,辅警缺乏统一的经费渠道和足额的经费保障,存在财政全额保障、财政部分保障、公安机关自行保障等多种形式。此外,我国目前的警力供给还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可以是多元化、多渠道的供给方式,包括将公共安全人员的薪酬养老方式由政府直接供养改为间接供养、均等制改为竞争制、终身制改为任期制等。除了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造成的安全事件相对难以预测,我国的公共安全隐患主要是在东部发达地区,譬如江苏苏州警察有1万2千名,没有编制的警务辅助人员有3万6千名,共同承担着打击占全省近三分之一的违法犯罪案件的重任。这些地区可以根据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下“属地管理,分级负担”的公安经费保障原则,将辅警支出纳入财政预算,由县(市、区)级财政负责。在江苏的苏中和苏北,由于地方财政并不富裕,在同样需要警务辅助人员提供公共安全的情况下,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就非常重要,否则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地方警察机构就会寻找灰色经费以维持运转。因此,一方面是建立稳定的地方经费保障机制,另一方面则是人事编制权力的适当下放,允许地方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财政供养的公共安全人员的数量和年度调整幅度。
第二,针对公共安全支出的信息公开不足,明确公共安全的支出科目。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公共安全支出科目应该具体明确。在目前的公共安全支出中,大部分支出是与主流国家一致的,也有少部分科目具有中国特色。公共安全支出中一个较大的科目是人员和办公经费,在公共安全系统内存在编制内和编制外联众用人方式的情况下,必须明确不同类型的人员经费来源及支出并予以财务信息公开。美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通常按照机构运行经费和资本项目支出进行分类,机构运行经费预算通常涵盖12个月,其中包括诸如工资薪金、员工福利、办公设备开支、电话服务费等项目。资本支出预算又称做基础设施改善预算。各地的财政部门为如何准确划分机构运行经费预算和基本建设改善预算提供了指导方针。整个预算计划大约有80%或更多的篇幅都是关于员工及其所需开销的,如工资薪金、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养老金计划、加班费及训练经费,并且通过分项列支预算、项目预算、绩效预算、零基预算和混合预算五种方式进行预算控制。
第三,针对公共安全支出的扩张,积极引进公共安全的多元供给。我国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对着众多复杂的危机挑战,包括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因此公共安全支出短时期内依然会维持高位运行,积极拓展公共安全的多元供给势在必然。改革的方法应该是在明确政府是公共安全主要供给者的前提下,打破公共安全只能由政府提供的陈旧思维,引入不同体制的主体共同参与供给。由于我国的公共安全支出整体很高,上升幅度也比较快,因此理性控制其规模和增幅实属必要。对于开放式的公共领域和公共场所安全,主要应由公共财政承担;对于半开放或者纯粹私人的领域和场所,由于不了解受益者的个性化安全需求,公共财政不能越俎代庖,而应该允许私营的保安、物业、特勤等公司或者个人提供安全,受益者额外买单承担成本。在近现代西方,面对来势汹涌的犯罪浪潮,警力资源捉襟见肘,为有效提高对犯罪的预防与控制能力,会采取安全承包的方式,将很多不属于政府严格管控的领域放开,交给私营企业承担安全责任,比如伦敦奥运会的安保就是由大量的私营企业参与,在开闭幕式这样的重要场合,官方的警力也远远少于我国。为了增补公共安全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会提供补助、接受捐赠项目和筹资项目,采取使用者付费或警察服务收费的方法。至于在我国饱受质疑的罚没财产,美国警察则奉行实用主义,除了罚没资金必须上缴以外(视情况返还),警察可以保留罚没物并加以使用。
责任编辑 廖朝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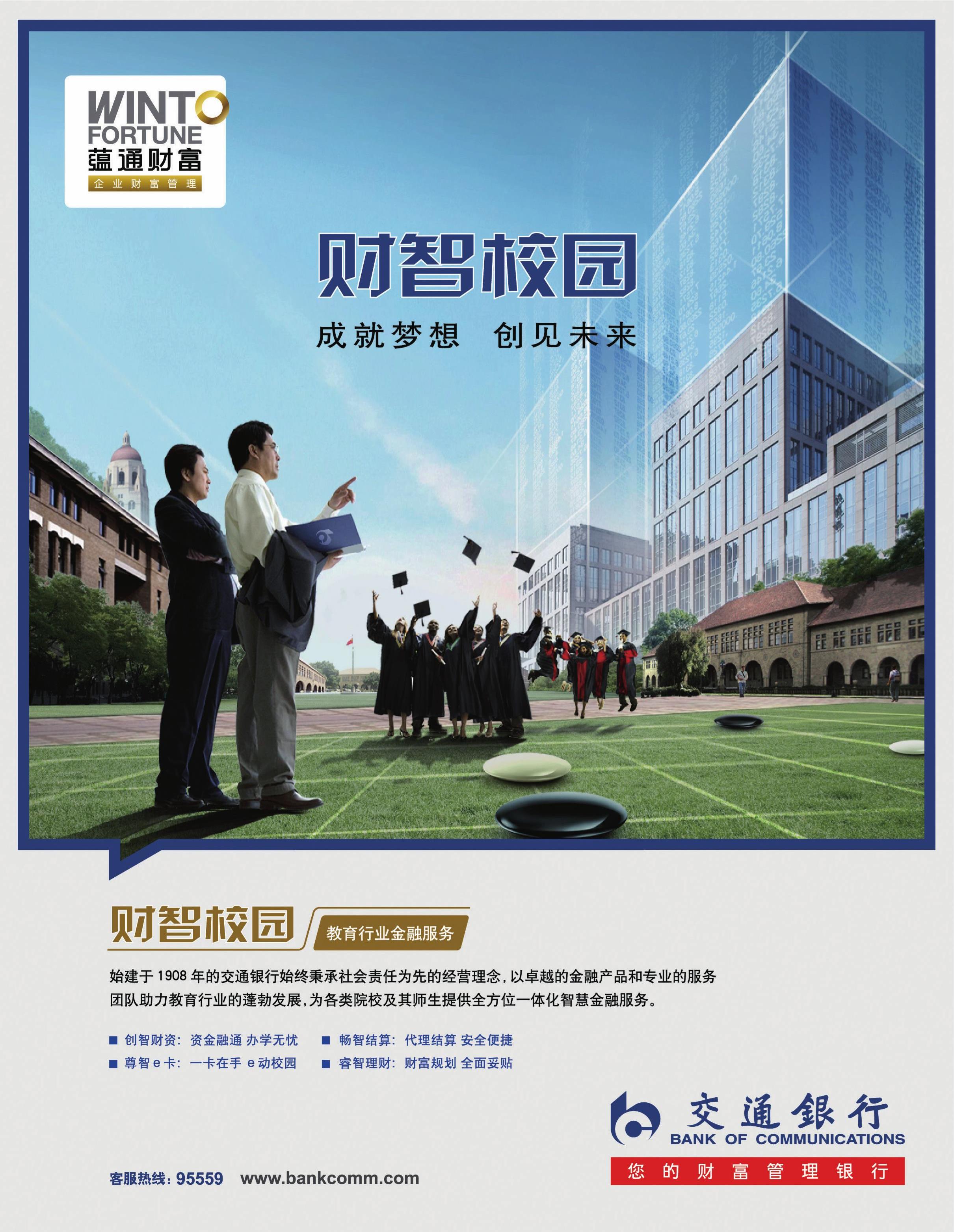
 附件下载:
附件下载:相关推荐
-
无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