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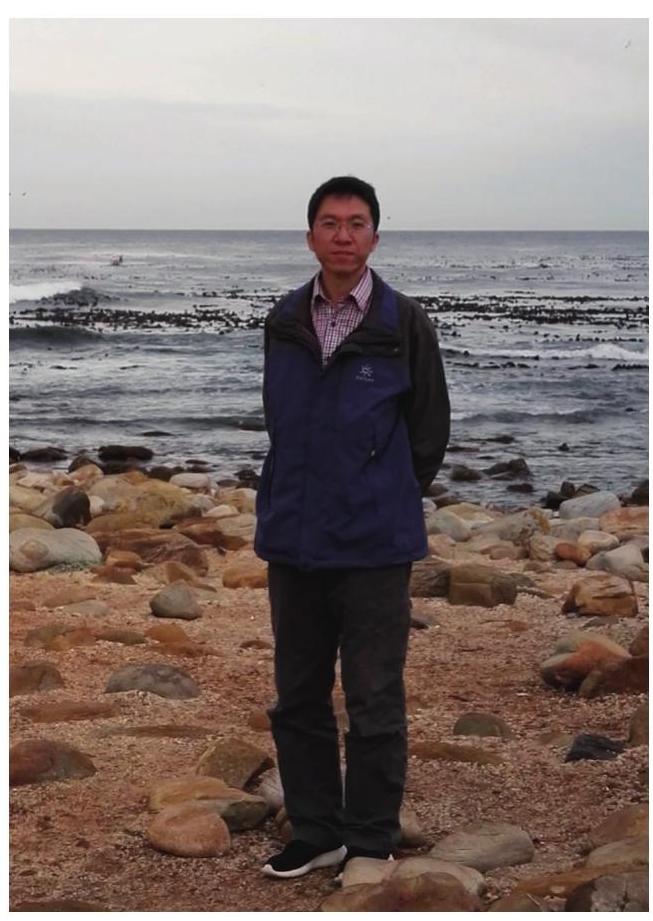
《中国财政》于我,是满满的回忆,是深深的感恩,是很想很想的想念。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2005年的秋天,我正准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财政部科研所作为财政部智囊机构,非常注重政策研究,在招收研究生时也更关注报考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中国财政》作为财政机关刊物,其刊载的文章贴近实践,政策性强,文风朴实,正是应试者的“红宝书”。我认真研读了2005年全年和2006年1—3月《中国财政》上的所有文章,在后来的入学考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那以后,我都会为准备报考财政部科研所的同学推荐《中国财政》,自己也把《中国财政》视为精神食粮。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第二次的亲密接触。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我撰写了一篇名为《减少我国贸易顺差的财政政策选择》的学术论文。当时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拿出去发表,而自己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财政》。但之前从未在财政类核心期刊发表过文章,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中国财政》编辑部投了稿,本来是做好了石沉大海的准备,没想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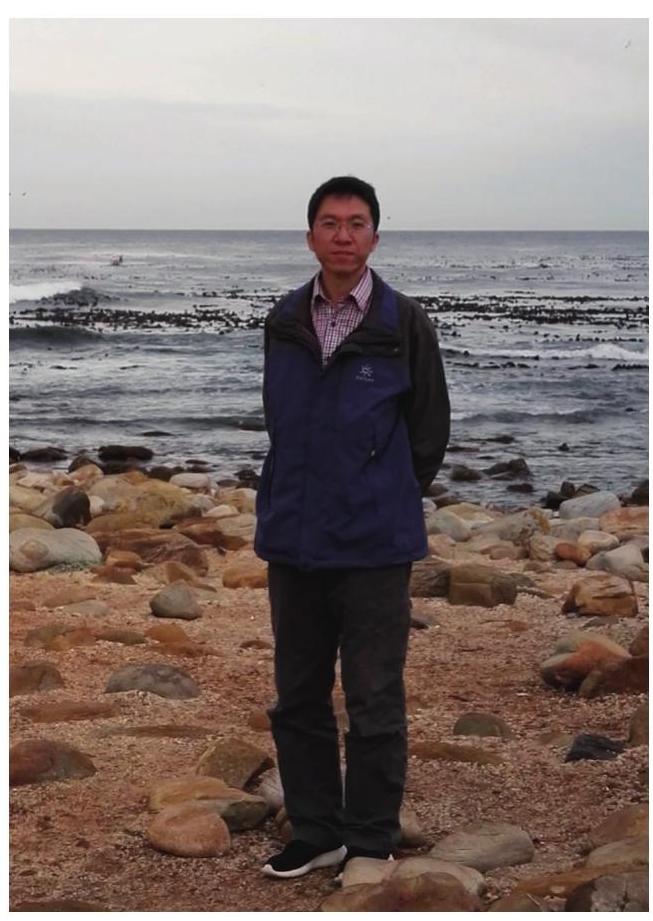
《中国财政》于我,是满满的回忆,是深深的感恩,是很想很想的想念。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2005年的秋天,我正准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财政部科研所作为财政部智囊机构,非常注重政策研究,在招收研究生时也更关注报考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中国财政》作为财政机关刊物,其刊载的文章贴近实践,政策性强,文风朴实,正是应试者的“红宝书”。我认真研读了2005年全年和2006年1—3月《中国财政》上的所有文章,在后来的入学考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那以后,我都会为准备报考财政部科研所的同学推荐《中国财政》,自己也把《中国财政》视为精神食粮。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第二次的亲密接触。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我撰写了一篇名为《减少我国贸易顺差的财政政策选择》的学术论文。当时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拿出去发表,而自己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财政》。但之前从未在财政类核心期刊发表过文章,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中国财政》编辑部投了稿,本来是做好了石沉大海的准备,没想到居然发表了!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编辑部的陈素娥大姐打电话让我领杂志和稿费,我是好几天晚上都激动得睡不着觉,那本2007年的旧杂志直到今天都是我手里最珍贵的“典籍”。
第三次的亲密接触。从财政部科研所毕业后,我有幸到中国财政杂志社工作,成为财政编辑中心的一名编辑。从读者到作者,再到编辑,就像从相识到相恋,再到相爱,我把《中国财政》融进了自己的血液里。在杂志社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参与了共48期《中国财政》的编辑出版工作,从约稿、审稿、撰稿,到编辑、配图、排版,再到一校、二校、三校……上百篇、过万字的文章都是华彩乐章,都是曼妙音符。这期间,我自己也撰写了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中国财政》上。2011年,我又荣幸地赶上了中国财政杂志社成立30周年,我为自己是这里的一份子而深感自豪,也是在这一年,带着依依不舍,我离开了杂志社到国家旅游局工作。《中国财政》编辑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如人之初恋,美好永存,无可替代。
第四次的亲密接触。到国家旅游局工作后,我更多的工作是部门预算和旅游管理,但一有时间我就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财政》,看上面的文章,看编辑人员的名字,回忆那些一起战斗的日子。2013年,我撰写了一篇旅游业税收政策方面的论文,发表在《中国财政》上。正是这篇偶然的无心之作,使我侥幸成为了2014年度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对象。5年来,我没有离开过《中国财政》,她也没有离开过我。
从2005年算起,10余年来,《中国财政》引导着我成长,也记录着我的足迹,她是我的教科书,也是我的日记本。我坚信,我与《中国财政》还会有第五次、第六次、第N次的亲密接触。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流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流泪,因为你在我心里。
值此《中国财政》创刊60周年,衷心祝愿《中国财政》图强图变,求实求新,越办越好!
责任编辑 李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