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1988年第04期 > 中国财政1988年第04期文章 > 正文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1988年第04期 > 中国财政1988年第04期文章 > 正文自负盈亏的“自”,究竟指的是谁?
时间:2020-05-06 作者:唐生
[大]
[中]
[小]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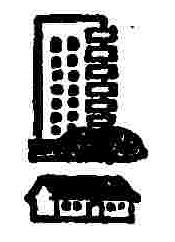
增强国营企业的活力,是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搞活企业中,人们对国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多有议论,主要是觉得企业只能负其盈,不能负其亏。其所以如此,有的同志认为主要是所有制问题,因而把改革所有制作为深化企业体制改革的关键或核心。改革所有制的方案有种种,概括起来不外多种形式的股份制(有人认为这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必然结果)。有的主张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下放给企业的自有资金,以及由此新增的资产,实行资金分帐制度,把全民财产分成国家股和企业股,然后按股分红。有的还建议增加职工个人股份,实行国家、集体、职工三种股份,按股分红。甚至有的文章干脆主张,把国营企业财产的一部分(大约占全部财产的50%)所有权无偿转让给企业,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企业集体股份(约占全部财产的30%),另一部分无偿转让给职工作为个人股份(约占全部财产的20%)。也有的走得更远一点,认为应当逐步过渡到政企分开的企业所有制,取消全民所有制,如此等等。按此思路推演下去,为了使企业能负其亏,似乎只有把全民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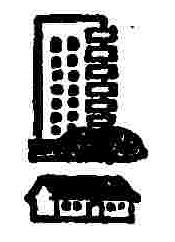
增强国营企业的活力,是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搞活企业中,人们对国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多有议论,主要是觉得企业只能负其盈,不能负其亏。其所以如此,有的同志认为主要是所有制问题,因而把改革所有制作为深化企业体制改革的关键或核心。改革所有制的方案有种种,概括起来不外多种形式的股份制(有人认为这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必然结果)。有的主张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下放给企业的自有资金,以及由此新增的资产,实行资金分帐制度,把全民财产分成国家股和企业股,然后按股分红。有的还建议增加职工个人股份,实行国家、集体、职工三种股份,按股分红。甚至有的文章干脆主张,把国营企业财产的一部分(大约占全部财产的50%)所有权无偿转让给企业,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企业集体股份(约占全部财产的30%),另一部分无偿转让给职工作为个人股份(约占全部财产的20%)。也有的走得更远一点,认为应当逐步过渡到政企分开的企业所有制,取消全民所有制,如此等等。按此思路推演下去,为了使企业能负其亏,似乎只有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成集体所有制、半私有制、私有制或名公实私才能办得到。因为最典型的自负盈亏的是私营企业。这样的思路,简直要把人引入歧途。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把人弄糊涂了,即:究竟谁是全民财产的所有者,自负盈亏的“自”究竟指的是谁?《红旗》杂志1988年第一期佐牧同志的“谈谈股份制几个理论问题”一文,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它只能指所有者而不能是企业集体或企业职工。它的含意是企业亏损或破产时,所有者在注册资产总额的界限以内承担有限的清偿责任,盈利时则以所有者的资格获得企业的利润。”如果自负盈亏的“自”是指企业,那么,由国家投资的国营企业,盈利却为企业这个集体占有、支配和使用,那同集体所有制还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文化大革命”前,在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时候,有人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如实地称为“自计盈亏”。佐牧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企业经理人员是以自己的经营管理才能,接受所有者的委托主持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的。他不是所有者,也无本可亏。劳动者只能对他接受的劳动任务负岗位责任,而不能对企业的盈亏负责”。当然,在当前体制下,企业和职工也不是对企业的盈亏毫不挂钩。盈利了经济效益好,税后留利的一个适当比例可以用于发放奖金,或工资上浮。亏损了,经济效果差,奖金不发,甚至工资下浮,企业经理人员也可能降级或免职。事情很清楚,自负盈亏的“自”指的是所有者,盈利了,所有者得大头;亏损了,甚至破产了,损失最大的也是所有者,这是很自然的。即使是最典型的自负盈亏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是指的股东,而不是经理和职工。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其他问解也就容易回答了。
可不可以把企业的留成资金以及用留成资金新增的固定资产,归企业所有,并按股分红?不可以。全民资产绝不是无主资产。把资产所有权下放给企业,并按股分红,企业职工就会以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利润的分红,就会在劳动报酬以外得到一份股份红利的收入。因此,这已经不是体制的改变,而是经济利益的调整和所有制的改变。新增资产也应属于所有者,因为追求资产的不断增值,正是投资者的动机,香港人叫做“投资回报”。1987年6月4日《经济日报》刊载薛暮桥同志的文章,以首都钢铁公司为例,8年来留成资金和由此创造的资产已达9亿元,接近于原有的财产,如果都归企业所有,再过若干年首钢将变成集体所有制企业了。首钢领导同志明确表示,新增资产应是国家的财产,首钢要保持国有性质。
用银行贷款新增的固定资产是否可以成为企业的财产?不可以。薛暮桥同志的文章认为,西方国家的资本家用自己的财产担保(抵押)向银行贷款,还本付息以后就成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同样,国营企业由国家或以国有财产为担保取得银行贷款,还本付息以后新增的资产应归国家所有。何况现在是税前还贷,更应如此了。
使企业和职工分得一部分股权,不是可以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吗?这要具体分析。佐牧同志的文章认为,劳动者同时又是他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是小生产的特征,而决不是现代化大生产的特征。对那些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型企业,采取群众入股方式,使劳动者成为本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有重要意义。但对于国营的现代化的大中型企业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同提高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按照现行体制,国营企业职工已经有了税后利润的分享权,职工收入同企业效益挂钩,这不是按股权而是按劳动贡献分配的,属于个人消费基金按劳分配性质。这种办法更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有什么理由使个人消费基金由按劳分配变成按资分配呢?退一步说,即使把国营大中型企业变成群众股份企业,能否保证防止企业短期行为,是否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都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有的也有职工认购的股份。在开放股票市场和股票自由买卖的条件下,职工所关心的是股票的行市和买卖,并不一定关心企业的经营。至于那种主张把国营企业财产的一部分所有权无偿转让给企业作为企业的集体股份,一部分无偿转让给职工作为个人股份,薛暮桥同志的文章认为这是公然侵犯国家公共财产,是违反宪法“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的。
有人认为,全民资产划分为国家股和企业股,企业可以据此获得收益,也可以有偿转让,但不能无偿转让化为私人或集体的财产,企业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仍归于国家,这有何不可呢?这个说法忽略了终极所有权必须获得经济利益和承担经济责任这一基本原则,竟认为终极所有权可以不通过获得利润而仅仅是通过法律来实现。这样,国家对企业股资产的终极所有权将变成名义的所有权,而企业作为法人对国家资产的名义所有权将变成实际的所有权。这是不正确的。
如此说来,国营企业是否根本不能实行股份制?那也不是。海外有的学者把股份制等同于私营化,把我国社会主义股份企业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那是不恰当的。当然,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应当是有选择和有限制的。公股联营,包括中央和地方联营,地方和地方联营,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联营等,将是股份制的重点,发展前途最大。个人入股,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股份公司的性质,把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产用股份形式转让给内部职工或外部认股者,这有可能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可以个别试验,但不宜推行,特别是高盈利企业更不应搞。目前有的国营企业,由职工认购的股票,既拿股息,又得红利,“双保险”,使股票完全变了样。个人入股,股份制,在集体所有制企业或合作社社员所有制,以及城乡个体户的股份经营发展中,有广阔的天地。当然也要随着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自愿原则,逐步试行,不断总结经验,要避免因提倡“股份化”而形成“股份热”,甚至出现冒牌货,就象几年前曾在一夜之间出现的数以千计的不够格的“皮包公司”那样。
 附件下载:
附件下载:相关推荐
-
无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邮编:100036 电话:010-88227114
京ICP备1904795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 电话:010-88227114
- 邮编:100036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