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2002年第06期 > 中国财政2002年第06期文章 > 正文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2002年第06期 > 中国财政2002年第06期文章 > 正文“走出去”战略的国际经验
时间:2020-04-25 作者:张铁刚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大]
[中]
[小]
摘要:
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写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也发现,简单地追求吸引外资过度投资于内部也有副作用。为此,应该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部分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情况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为本国经济发展拓展运行空间,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经济体(即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带有共性的发展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逐次转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雁阵发展模式”。70年代初,日本开始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投资,大规模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后逐步扩大到全世界,投资行业范围也向多领域发展。截至1999年3月31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达到6570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投资金额为1994亿美元,比重占30.3%;非制造业投资金额4472亿美元,比重占68.1%。就地区而言,日本对欧美等发达...
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写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也发现,简单地追求吸引外资过度投资于内部也有副作用。为此,应该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部分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情况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为本国经济发展拓展运行空间,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经济体(即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带有共性的发展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逐次转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雁阵发展模式”。70年代初,日本开始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投资,大规模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后逐步扩大到全世界,投资行业范围也向多领域发展。截至1999年3月31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达到6570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投资金额为1994亿美元,比重占30.3%;非制造业投资金额4472亿美元,比重占68.1%。就地区而言,日本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商业和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投资比重较大,对亚洲地区则以纺织、机电等加工组装制造业投资为主,对中东、大洋洲、非洲等以资源、能源定向开发进口类型的投资较多。
80年代以后,香港、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台湾等开始向外扩张,成为新兴的对外投资力量,并且它们之间相互投资及对我国大陆的投资不断上升。截至1998年底,香港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1549亿美元、新加坡476亿美元、台湾380亿美元、韩国215亿美元、马来西亚146亿美元,印尼和泰国也分别达到21亿美元。在逐步实施资本项下可兑换的基础上,有关国家和地区大力开发海外金融市场,推动金融国际化,金融与贸易、投资齐头并进,相互促进。日本泡沫经济破碎之前,其海外金融机构遍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海外金融资产一度占世界各国金融机构海外资产总额的38.2%,对外债权额占世界债权市场份额的36%,一度高居世界首位。
近年来,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兴起,服务业和信息产业逐渐向外扩展的趋势十分明显。200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在信息产业的过度投资,美国的新经济开始出现调整,有关信息产业的技术和资本外溢速度加快。受劳动力成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新一轮的生产转移开始形成。新兴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传统产业分工体系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
二、“走出去”的国际经验
第一,建立促进和保障“走出去”的法律体系。日本为了更好地发展外向型经济,制定了《进出口交易法》、《贸易保险法》、《贸易保险特别会计法》、《出口信用保险法》、《外汇和外贸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涵盖了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方方面面。韩国政府从70年代起开始专门制定了《扩大海外投资方案》、《外汇管理规程》等法规条例。通过一整套系统的法律及政策安排,有关国家不但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明确了海外投资的基本战略,而且也使得海外投资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切实维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第二,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对于新兴国家而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根本无法同发展了上百年的跨国公司相比,因此这些国家的企业要想“走出去”、“站住脚”,就必须给予政策支持。而税收是政策支持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税收优惠,政府通常可以诱导企业更好地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意图。日本、韩国对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从事资源开发和境外加工的企业,给予了相当优惠的免税、减税和出口退税待遇。
第三,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海外投资的很多风险是企业无法独自承担的,但是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战略意图,又需要企业去开发风险较高的市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很多国家以各种形式设立了海外投资风险基金。例如,日本有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资金由政府和参与该制度的企业分摊。在一定标准内,企业海外投资的部分损失可以得到补偿,因自然灾害、战乱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损失还可享受高比例补偿。参与准备金的企业还可以提用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作为海外再投资。又如,隶属美国联邦政府的私人海外投资公司(OPIC)有专门从事为政治风险担保的业务,对于货币不可兑换、财产被没收以及政治动乱等三种原因给海外投资公司造成的损失,给予一定补偿。
第四,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都需要一定金融支持。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通过进出口银行、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等金融网络,以出口信贷、出口信贷保险、援外优惠贷款等形式,全力支持企业海外投资。日本、韩国等均建立了便捷实效的海外投融资制度和保险制度,政府、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分担企业投资风险,为企业投融资提供便利。美国政府下属的进出口银行专门承担商业银行无法承受的风险,以避免与商业银行发生不必要的竞争,同时使美国海外投资企业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接受资金支持。
第五,逐步减少投资限制,简化审批程序。发达国家在“走出去”过程中,限制相对较少。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外汇等相对比较稀缺,而且为了实施“赶超战略”,要集中使用各种资源,因此在“走出去”的初期都进行了较为严格的管制。日本、韩国等,都经历了从投资管制到投资自由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关国家和地区加快了为企业“松绑”的步伐。目前,日本和韩国已废除了外汇管制,基本取消了对海外投资的各种限制。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等都已经将超大型投资项目审批制改为事后备案制。
第六,放宽对人员出入境的限制。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走出去”,最终都要落实到“人”。因此,影响走出去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人员的自由流动。东亚国家和地区随着自身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涉外经济管理的逐步变革,逐渐放宽了对公民出境的限制,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鼓励公民合法出境的政策,公民无特殊情况均可在最短时间内取得因私护照。普通商务往返和劳务输出则一般不用审批,也不会附加任何出境限制。与此同时,世界上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相互之间积极磋商达成互免签证协议。
第七,对资源开发型和科技开发型投资予以特殊扶持。很多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由于自然资源相对比较贫乏,政府对本国或本地区在海外从事资源开发和科技开发的企业均提供了政策性贷款或补贴,并指导银行对这类项目提供优惠贷款,海关对这些企业在海外开发并输送回国内或区内的资源性产品进一步减免关税。日本政府成立了“金融矿产事业团”,以官企合资形式,对海外资源勘采给予融资支持,对战略矿产(如铀矿)的勘探实行特别贷款制度,还款期最长可达18年。
第八,完善信息服务。各国、各地区在实施“走出去”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发布工作。政府除了充分发挥其驻外使领馆和代表机构的窗口作用外,还充分地调动各种进出口商会、国内外行业协会、外国企业协会和大型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其专业性强、联系面广,信息灵通的优势。日本贸易振兴会就派驻了遍布世界各地的机构,主要进行与贸易有关的调查研究,并受政府和企业委托推介本国产业及产品,效果相当不错。
第九,“走出去”必须在领域和地区上有所侧重。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在某一个时期有关“走出去”的支持政策是有所侧重的。在企业类型上,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资源贫乏的国家就重点鼓励本国企业进行所缺资源的境外开发,建立有利于带动出口的境外加工项目和境外科研中心等;在产业类别上,国内成熟和过剩的产业则通常是向外转移的重点;在策略上,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倾力扶持一两种产业,强化此类海外投资项目的国际竞争力;在地域选择上,资源开发项目一般集中在资源的主要拥有国,其他的“走出去”项目通常采用由近及远的次序,因为到地理距离比较接近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项目开发,不但具有一定的地缘优势,而且文化上一般也比较接近,沟通和交流的成本比较低,“走出去”的成功率比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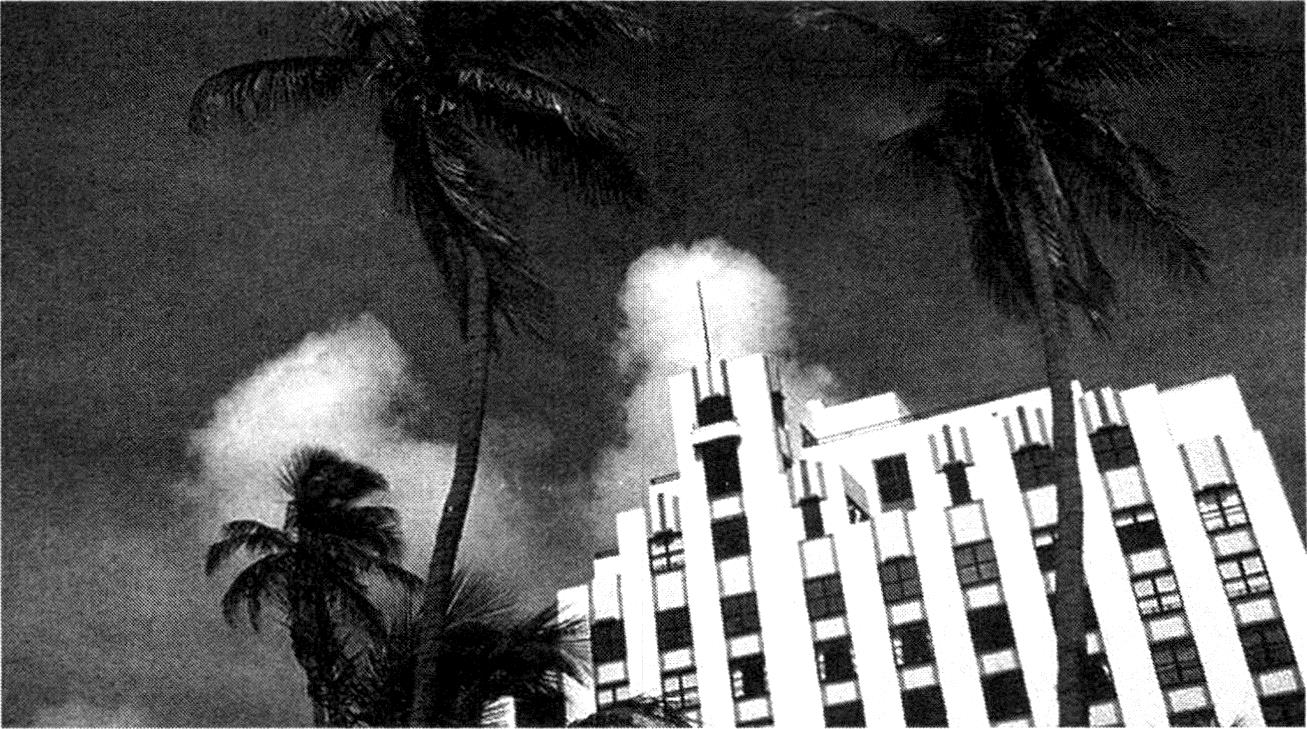
 附件下载:
附件下载:相关推荐
-
无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邮编:100036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40014 投诉举报电话:010-88227120
京ICP备1904795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投约稿系统升级改造公告
各位用户:
为带给您更好使用体验,近期我们将对投约稿系统进行整体升级改造,在此期间投约稿系统暂停访问,您可直接投至编辑部如下邮箱。
中国财政:csf187@263.net,联系电话:010-88227058
财务与会计:cwykj187@126.com,联系电话:010-88227071
财务研究:cwyj187@126.com,联系电话:010-88227072
技术服务电话:010-88227120
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财政杂志社
2023年11月
-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 投诉举报电话:010-88227120
- 邮编:100036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