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财务与会计过刊查询 > 《财务与会计》2016年第21期 > 财务与会计2016年第21期文章 > 正文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财务与会计过刊查询 > 《财务与会计》2016年第21期 > 财务与会计2016年第21期文章 > 正文“经济人”的道德基础——解读亚当·斯密《道德情感论》的一个视角
时间:2019-10-25 作者:吴大新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大]
[中]
[小]
摘要:
一、“经济人”的涵义
随着西欧商业社会的兴起,经济学在18世纪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如今,经济学的一些专门术语为社会科学各领域所广泛使用。“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或Economic Man)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概念之一。不过,概念的广泛使用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它的真正理解。直到现在,将“经济人”等同于“自私自利之人”的看法仍然存在。
实际上,“经济人”不过是要表明,市场上的人有自利(self-interest)的强烈本能,而且能够理性地作出行为选择。作为一种假说,“‘经济人’的核心命题是: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一命题在亚当·斯密(1723-1790)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第一次得到系统论证。其中,被广为引用的一句话是:“他通常确实无意于增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增进了多少公共利益。他……只是想尽可能增加他自己的利益;结果,在这种场合,和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宛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一个在其意图之外的目的。而且,社会也不会因为这个目的不在他意图之内而一定更糟...
一、“经济人”的涵义
随着西欧商业社会的兴起,经济学在18世纪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如今,经济学的一些专门术语为社会科学各领域所广泛使用。“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或Economic Man)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概念之一。不过,概念的广泛使用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它的真正理解。直到现在,将“经济人”等同于“自私自利之人”的看法仍然存在。
实际上,“经济人”不过是要表明,市场上的人有自利(self-interest)的强烈本能,而且能够理性地作出行为选择。作为一种假说,“‘经济人’的核心命题是: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一命题在亚当·斯密(1723-1790)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第一次得到系统论证。其中,被广为引用的一句话是:“他通常确实无意于增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增进了多少公共利益。他……只是想尽可能增加他自己的利益;结果,在这种场合,和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宛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一个在其意图之外的目的。而且,社会也不会因为这个目的不在他意图之内而一定更糟。经由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往往会比他真想增进社会利益时更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
斯密在此要表达的是,个人在公平地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既不需要政府的引导,也不需要个人显示出其“仁爱”之心,仍然完全可以增进社会利益。但这种表达往往被人视为“经济人”自私、冷漠的证据。持这种看法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了解斯密《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的基本原理。实际上,在该著中,斯密已经为“经济人”奠定了宽宏的道德基础。
二、解读《道德情感论》
(一)对《道德情感论》的一些误解
受日本学界的影响,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长期被误译为《道德情操论》,可谓流毒甚广。实际上,sentiments在斯密的语境中是指一个人由某事物或行为所引发的种种情感或感受,它并非专指高尚的、崇高的情感,因此,该词应译为“情感”(或“感情”)而非“情操”。《道德情感论》是伦理学著作,我们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将其视为一本“修身书”。二战前,日本学界在翻译方面的谬误非常多见,张东荪先生曾对此进行过严厉批判。他说:“向来中国对于西方思想之输入多借助于日本,于是满纸但见生澁不通之日本译名。”但二战后,至少在斯密研究领域,日本学界已对前述错误作了根本性的修正,现在通常将其译为《道德感情论》。第一位准确解读斯密思想的中国学者大概是张东荪先生,在其1934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中,该著即被译为《道德情感论》。另需注意的是,台湾学者谢宗林也将其译为《道德情感论》,由(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然而当该出版社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发行简体中文版时,书名却被改为《道德情操论》,令人遗憾。
(二)《道德情感论》的理论逻辑
在该著作中,斯密系统探讨了“什么是美德”、“美德从哪里来”等根本性的问题。他指出,“自利”(或“自爱”,self-love)毫无疑问是人的第一本性,因为人为了生存,必须要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时,“自利”既可能无碍于他人,也有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但人类所具有的“同感”(sympathy,将心比心、同情共感)能力,使得个人在行事时必须同时考虑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就像有一个“公正的旁观者”(the impartial spectator)在始终注视着自己一样(用现代的话说,社会舆论始终对个人行为实行监督),这样,他就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为他人所接受。当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按此行事时,就会形成一套为公众普遍接受的“一般规则”。这就是斯密所发现的社会合作机制(东荪先生曾对这一机制作了非常精到的概括——“我有行为必常衡以他人之好恶,人有作为亦必考之我之毁誉。于是人我之间息息相通。”)斯密进一步指出,这些一般规则同法律一样,是指导人们自由行动的准则;它由一个合法的上级制定,并且还附有赏罚分明的条款。
斯密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端赖于对“一般规则”的遵守。遵守“一般规则”,是“正义”(justice)美德的要求;不遵守“一般规则”,就是违背正义。而“由于违背正义是人们绝不肯彼此甘心忍受的行为,所以,行政长官不得不运用国家整体的力量强制人们实践正义的美德。没有这个预防措施,公民社会将会变成一座流血混乱的舞台,每一个人每当自认为受到伤害时便会以他自己的双手来报仇雪恨。”这样,“正义”就成为社会的基石。显然,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设定“一般规则”,并绝对保证这些体现正义要求的规则不被践踏。
我们还需同时看到,“正义”毕竟只是一种“消极美德”,因为它只是“阻止我们伤害邻人”;换句话说,要想达到正义的全部要求,只需“端坐无为”(sit still and doing nothing),即不触碰“一般规则”这一底线。不过,仅有“正义”只能形成一个冷冰冰的而非温情脉脉的社会。这样一个缺乏“仁爱”(benevolence)美德的社会,其实并非斯密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也许是斯密相信,只要正义得以伸张,仁爱就会随之而来。应该说,斯密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例表明,一个政治修明、法治健全的社会,也必定是一个充满仁爱之心的社会。因此,斯密只是将“仁爱”视为一种辅助性的美德,对它的论证也颇吝笔墨,而对“正义”这一主要的美德,斯密则非常详尽地加以论证(需要注意的是,斯密还准备写两本书,其中一本即准备对“正义”作更为详尽的论证,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了)。在他看来,“仁爱”只是建筑物的装饰品,而“正义”则好比一座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柱子松动了,人类社会这个巨大建筑就必然顷刻间土崩瓦解。因此,他强调,违背正义之举必须受到惩罚,而践行仁爱者则必须受到奖赏。这就是“上苍的伟大法则——投桃报李、以牙还牙”。他还不忘提醒说,仁爱是万万不能强求的。因为,“在立法者的所有责任当中,也许就数这项工作,若想执行得当,最需要大量的谨慎与节制了。完全忽略这项工作,国家恐怕会发生许多极其严重的失序与骇人听闻的罪孽,但是,这项工作推行过了头,恐怕又会摧毁一切自由、安全与正义。”
以上是斯密早年关于个人行为与社会秩序理论的基本逻辑,即,在政府制定的正义的法律保护下,人通过生而具有的“同感”能力合理地划定“群己权界”,个人的利己行为就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在此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会既符合自身利益,又增进公共利益。可以说,前五版的《道德情感论》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一种对新兴商业社会的乐观态度。
不过,斯密在晚年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他发现,“在制造业方面很有进展的大乡村的居民,往往由于公侯贵族卜居其间,而变得懒惰和贫困”。他还看到,商人和制造业阶层通过操控社会舆论与政府“联手”。他在与友人的信中气愤地写道:“在喧闹的反对声常常威胁政府,派系常常压迫政府的国家里,商业法规通常是由那些热衷于搞欺骗和向人民横征暴敛的那些人所口授的。”物质财富腐蚀着人们的良心,贫富分化瓦解了人们的信念,社会“风尚”只向富人和大人物看齐,“公正的旁观者”失去了公正,而当初被许以厚望的商业社会,也越来越失去通向“理想社会”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在这种苦闷的情绪中,斯密开始大幅改写《道德情感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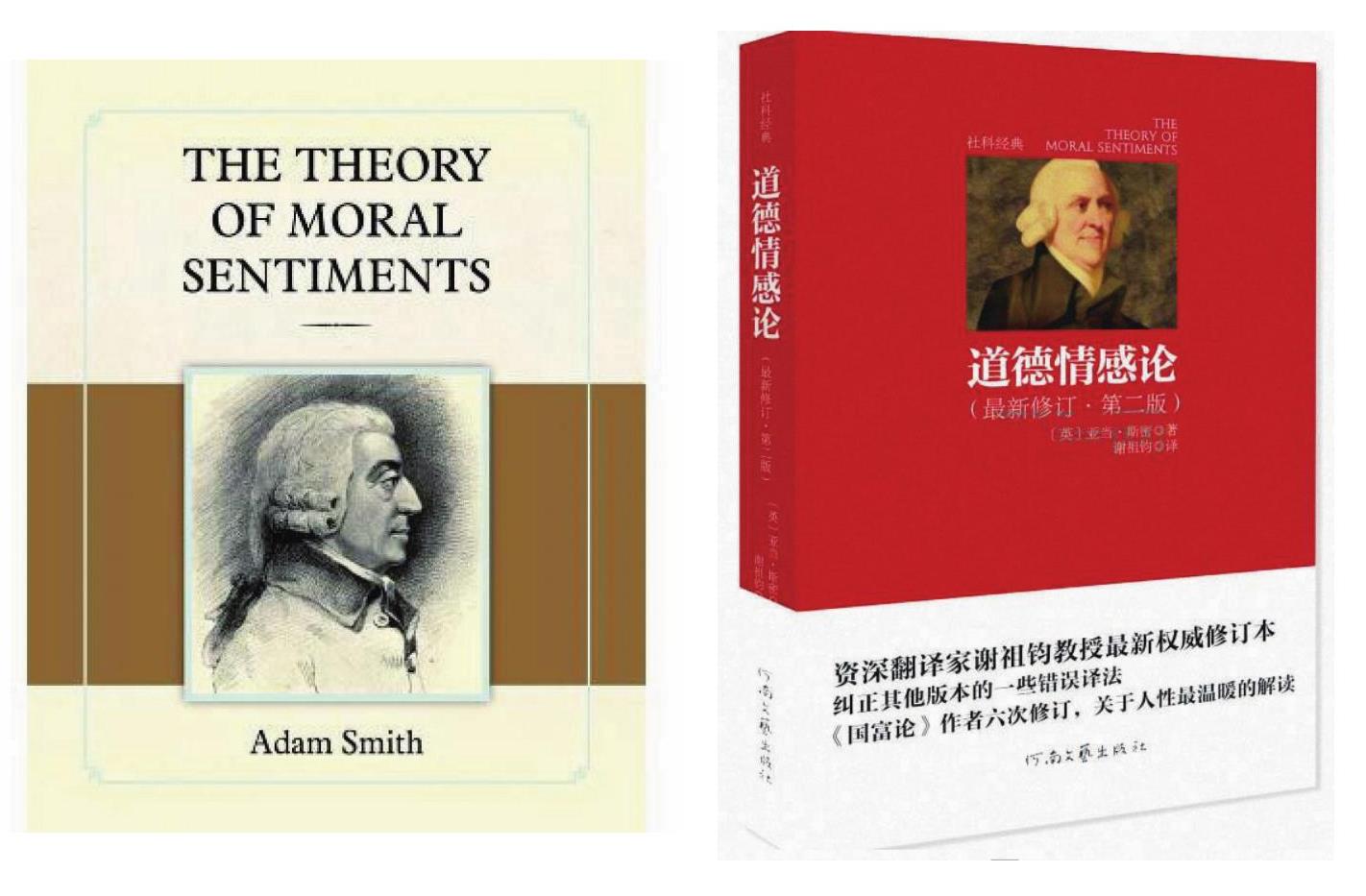
当然,斯密也指出了社会秩序混乱的另一根源,即政府的不作为或为所欲为。他认为,政治腐败是一切社会腐败的总根源。那么,在政府已经被证明不能指望的前提下,又如何去改变这一局面呢?无可奈何之下,斯密只好求助于“克己自制”(self-command)这一美德——一种“最伟大和最可贵的”美德。这时,他将“公正的旁观者”分为两个人——“外部那个人”(社会舆论)和“内心的人”。显然,当社会舆论开始沉沦,“外部那个人”也就不能指望,但他也清楚地知道,仅靠“内省”是不够的,因为“克己自制……远非凡人的菲薄力量所能做到”,它犹如“阳春白雪”般难以普及众生。但他之所以知其不可而为之,也许只是为了表明,“所有角色中那最伟大与最高贵的角色”,即“国家的改革者与立法者”必须具备这样的美德,因为,只有这一角色才能够做到,“以暗藏在那些被他建立起来的制度中的智慧,在他身后的世世代代,确保国家内部的和平与同胞们的幸福。”显然,斯密试图再一次强调公正的法律对“经济人”行为的约束以及社会正常运转的作用,虽然这一次他更寄望于“伟大的立法家”。
三、《道德情感论》的现时代意义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部写于两个多世纪前的著作时,仍能从中得到无限启发。一方面,由于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经济学的重大议题外,哲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乃至管理学等学科都可以从中找到相关议题。实际上,斯密理论的穿透力正源于他对社会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画。谁能否认,对人性的全面认识不是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首要前提呢?
另一方面,这种启发来自于斯密理论浓郁的时代气息。由于斯密的研究课题是市场社会中人与人的合作与社会发展,因此,只要一个社会仍处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中,他的理论就永远不会过时。就中国而言,市场取向的改革在上世纪末期渐趋深入,但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现象,这引发了学界关于“经济学是否讲道德”的大讨论。直到今天,这一讨论仍然在继续。鉴于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化的“大转型”中,这一问题仍需长期面对。就此而言,斯密《道德情感论》的主题可谓历久而弥新。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的人给出解决一切当代社会问题的现成答案,但至少,我们可以从斯密时代的老问题中得到新的启示。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对当代中国而言,我们仍需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保证“经济人”之间的合作。当然,这种合作只能建立在尊重“利己心”的基础上。制定和厉行“正义”的法律,促使“经济人”作出冷静的、理性的选择,培育其“谨慎”之德和公平竞争精神,仍是中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宣言。
 附件下载:
附件下载:相关推荐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邮编:100036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40014 投诉举报电话:010-88227120
京ICP备1904795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投约稿系统升级改造公告
各位用户:
为带给您更好使用体验,近期我们将对投约稿系统进行整体升级改造,在此期间投约稿系统暂停访问,您可直接投至编辑部如下邮箱。
中国财政:csf187@263.net,联系电话:010-88227058
财务与会计:cwykj187@126.com,联系电话:010-88227071
财务研究:cwyj187@126.com,联系电话:010-88227072
技术服务电话:010-88227120
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财政杂志社
2023年11月
-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 投诉举报电话:010-88227120
- 邮编:100036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40014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40014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