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2018年第24期 > 中国财政2018年第24期文章 > 正文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2018年第24期 > 中国财政2018年第24期文章 > 正文完善资源税改革的几点思考
时间:2019-10-23 作者:王萌 南京审计大学
[大]
[中]
[小]
摘要: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税制度,我国2010年率先在新疆开展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拉开了资源税制度改革的序幕。经过六年的探索实践,从2016年7月1日起,我国全面推开资源税改革,这是继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的又一项重大税制改革,对建设生态文明、节约资源有着重要意义。
以从价计征、资源税扩围和清费立税作为此次资源税费改革的方向,对进一步完善绿色税收制度,理顺资源税费关系,减轻企业负担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一是资源税收入快速增长,增加资源地财政收入,有利于建立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有利于增强地方保障民生等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改善地区发展环境。二是新一轮资源税改革对税费框架进行了重构,按照清费立税原则把清费和统筹税费关系作为重点,改变“税轻费重”现象,在提高资源税税率的同时,清理相关收费基金,进而建立功能明晰的资源税费制度体系。三是中央下放部分税政管理权给地方是此次资源税改革的一大特点。地方政府的作用受到空前重视,赋予地方较大的税政管理权。在不影响全国统一市场前提下,地方政府在资源税税率、征税范围和税收优惠三方面享有自主权,值得其它税种立法...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税制度,我国2010年率先在新疆开展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拉开了资源税制度改革的序幕。经过六年的探索实践,从2016年7月1日起,我国全面推开资源税改革,这是继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的又一项重大税制改革,对建设生态文明、节约资源有着重要意义。
以从价计征、资源税扩围和清费立税作为此次资源税费改革的方向,对进一步完善绿色税收制度,理顺资源税费关系,减轻企业负担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一是资源税收入快速增长,增加资源地财政收入,有利于建立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有利于增强地方保障民生等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改善地区发展环境。二是新一轮资源税改革对税费框架进行了重构,按照清费立税原则把清费和统筹税费关系作为重点,改变“税轻费重”现象,在提高资源税税率的同时,清理相关收费基金,进而建立功能明晰的资源税费制度体系。三是中央下放部分税政管理权给地方是此次资源税改革的一大特点。地方政府的作用受到空前重视,赋予地方较大的税政管理权。在不影响全国统一市场前提下,地方政府在资源税税率、征税范围和税收优惠三方面享有自主权,值得其它税种立法加以借鉴。但目前资源税改革进程中仍需完善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资源税主体功能定位。不同税种的主体功能定位是不同的,每个税种都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如果一个税种承担了太多的职能,尽管这些职能本身并不相互矛盾,也会导致税制设计无所适从,顾此失彼。梳理我国资源税历次改革发现,资源税设计目标呈多元化,并未突出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经济背景发生变化、资源定价体系的深化改革和资源开发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资源税从1994年以后尽管经历了数次调整,但其主体功能始终是定位于调节地租。即便是201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也是将资源税的功能定位于调节级差收入。2016年《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指出资源税在组织财政收入、调控经济、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发挥作用,较好地诠释了资源税的性质和目标。但并没有涉及到资源税的定位。资源税是定位于保护资源,促进资源的节约使用,还是原有的定位于调节级差地租,抑或定位于增加财政收入,《通知》没有明确。我国资源税设计的政策目标并未着重于资源的节约和可持续发展,而更多着眼于代内经济收益。
资源税调节级差收入在开征初期的特殊环境下是适合的,但现在已经不再适用,以后调节级差收入应交由资源采矿权价款实现;而从历年资源税占财政收入比重来看,资源税难担组织财政收入的大任;资源开采使用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应该由环境税进行调节。资源税应定位于对资源耗减价值的补偿,促进节约资源,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纯化资源税功能,剥离不适宜资源税承担的各项功能,将资源税从原来承担的多项功能中剥离出来作为资源耗竭性补贴,对资源开采的耗损价值进行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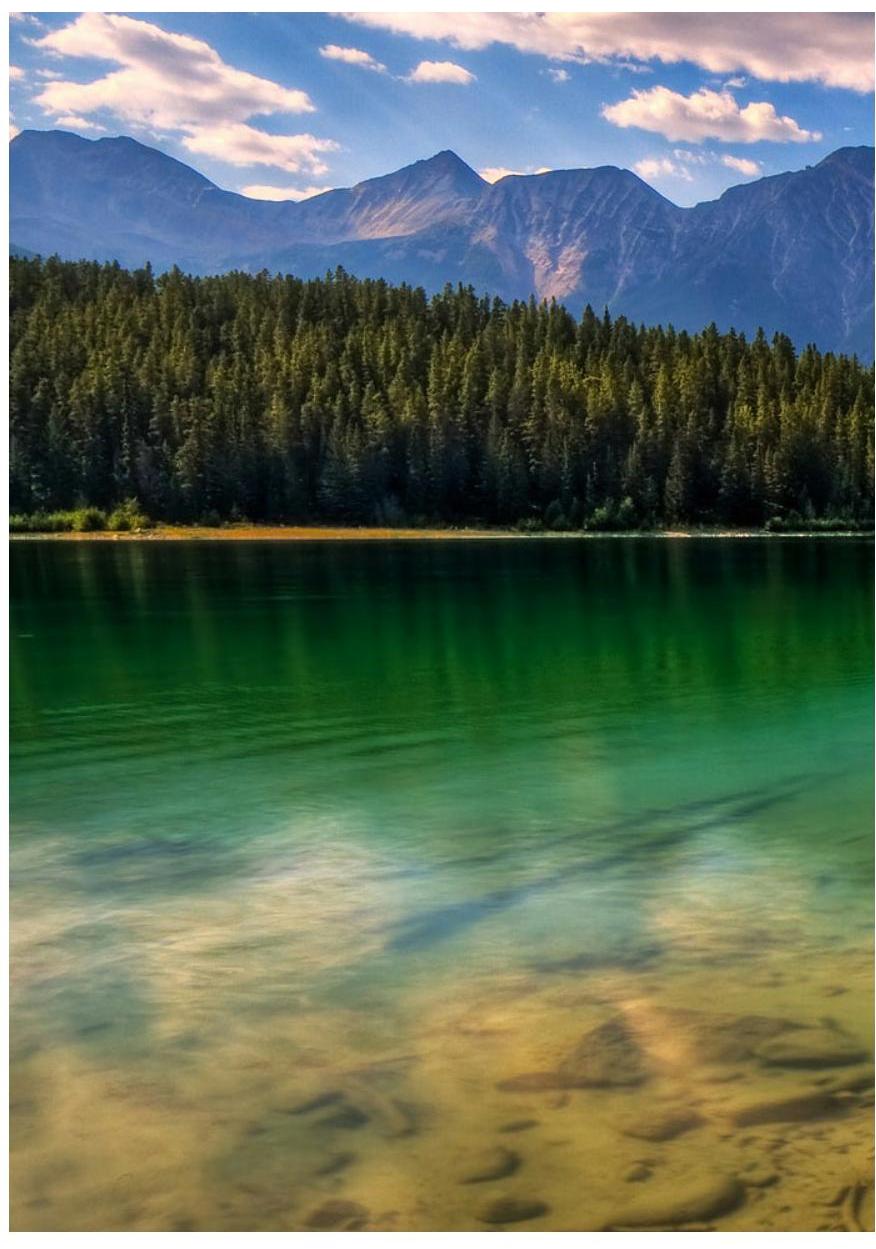
由于没有明确的主体功能定位,资源税在税制设计方面存在滞后性,缺乏前瞻性和引导性,不断摇摆,难以适应多变的客观形势变化。目前资源税改革依然“身兼数职”,并未明确资源税准确定位,使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资源税功能定位的复杂化、宽泛化、分散化不仅会增加税制的运行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使资源税改革最终成为被形势所逼的短期权衡决策,不是补偿代际外部性,而是着眼于代内经济收益。其后果是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问题的恶化。
合理定位资源税的政策目标,使征税范围、计税依据、税额设计、税权划分的设计原则统一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的核心政策目标,以“节约资源,保护生态”为核心政策目标,突出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避免资源税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避免具体税制设计的各个方面“各自为政”,互相“掣肘”。节约税制运行成本,增强其调节力度。
(二)推动资源税立法。资源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但缺乏有力的法律制度进行保障。我国目前关于资源税的最高法律文件是依旧是1993年出台的《资源税暂行条例》,法律效力较低。此次清费立税的依据主要来自于财政部的文件,其中财税[2014]74号文件规定:“在全国范围统一将煤炭、原油、天然气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财税[2016]53号文件决定:“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税费重叠、功能交叉问题,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等收费基金适当并入资源税,取缔违规、越权设立的各项收费基金,进一步理顺税费关系。”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开征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实际上是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取消了法律确定的费种。虽然这有利于当前的清费立税,但以突破法律界限的方式进行改革并不利于资源税的长远发展。
因此,在税收法定的理念下,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之后应加快现行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的调整。对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和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所不相适应的部分进行清理,并在适当的时候推动资源税立法进程,及时升级我国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形成一部比较规范和具有较高指导性与约束性的《资源税法》,通过立法升级,确实提高资源税实施的法律效力。
(三)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由于预算体制改革,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收入大多数实际上并未专款专用于生态保护,更多的是纳入到了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服从国家或地方财政大局,在全国或地区各类工作中统筹使用。随着“营改增”的全面实施,以及土地使用的规范化,资源税很有可能成为一些地方的主体税种,在资源税没有“专款专用”的制度保障情况下,资源大省的地方政府更容易对资源税收入产生依赖性。虽然根据预算体制改革要求,税收不能简单实行专款专用,但为确保后代人不会因为当代人的资源使用行为而利益受损,就需要在预算安排上,结合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加强资源领域的科技创新、新能源开发和资源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能源结构,从而保证后代人公平“享用”良好的资源。
责任编辑 雷艳

 附件下载:
附件下载:相关推荐
-
无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