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2015年第03期 > 中国财政2015年第03期文章 > 正文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2015年第03期 > 中国财政2015年第03期文章 > 正文《预算法》立法宗旨演进及其积极意义
时间:2020-02-12 作者:侯卓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
[大]
[中]
[小]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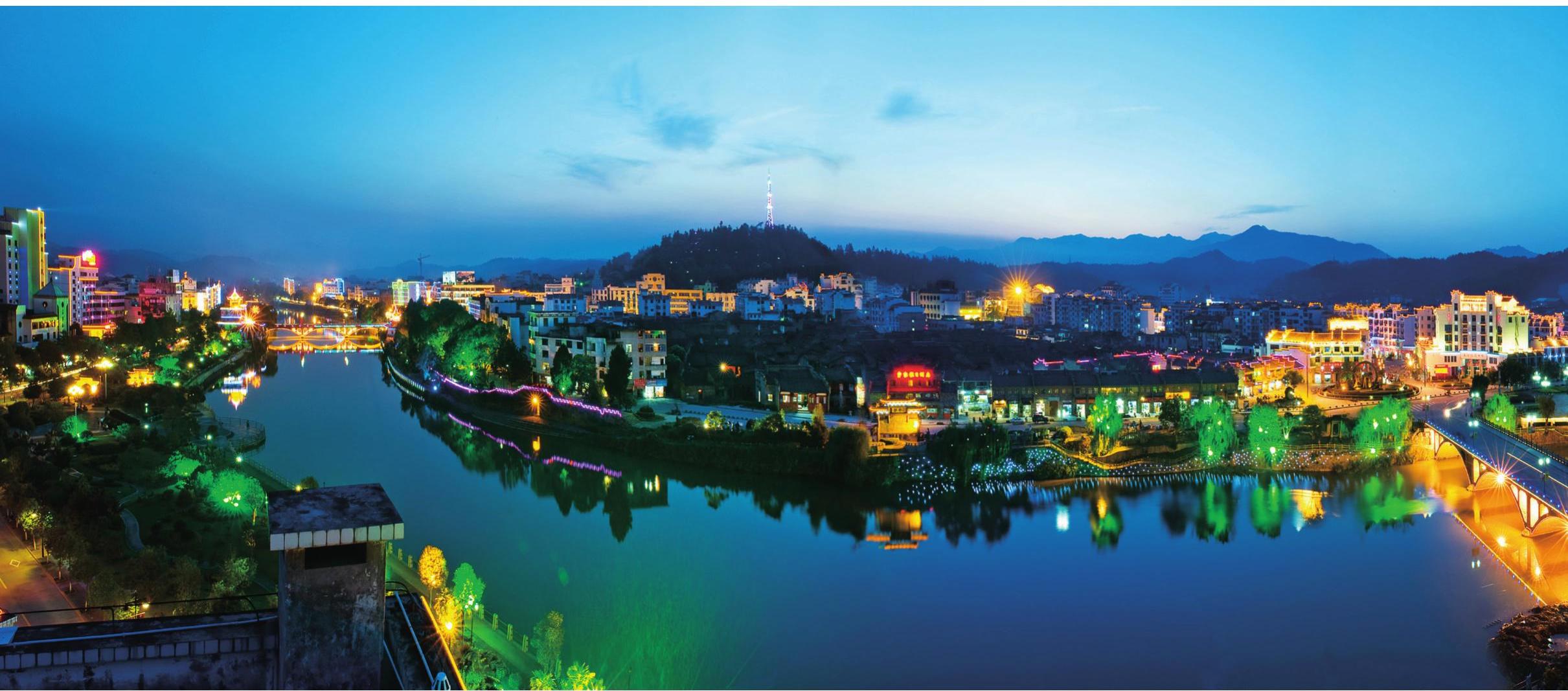
立法宗旨是一部法律的灵魂,对于具体制度的设计起到统领作用。在制定法律时,立法宗旨的确立十分关键。2014年8月通过的预算法修正案,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该法第一条“预算法立法宗旨”进行了修改。
本次《预算法》修改过程中,立法宗旨条款的修改经历了一些波折。修改前的《预算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此处的“国家”表述宏大,其法学意义可以解读为“政府”,那么这条规定显然是将预算作为政府管理社会、上级政府控制下级政府以及政府据以进行自我管理的工具。直至二审稿时,仍未对这一条进行任何修改。在二审稿向社会征求意见时,引发学者们较大议论。一致认为立法宗旨在整部法律中地位重要,如果仍坚持“管理”的定位,整部《预算法》修改所能达到的目标相当有限。2014年4月的三审稿中,对立法宗旨的规定发生根本性变化,该稿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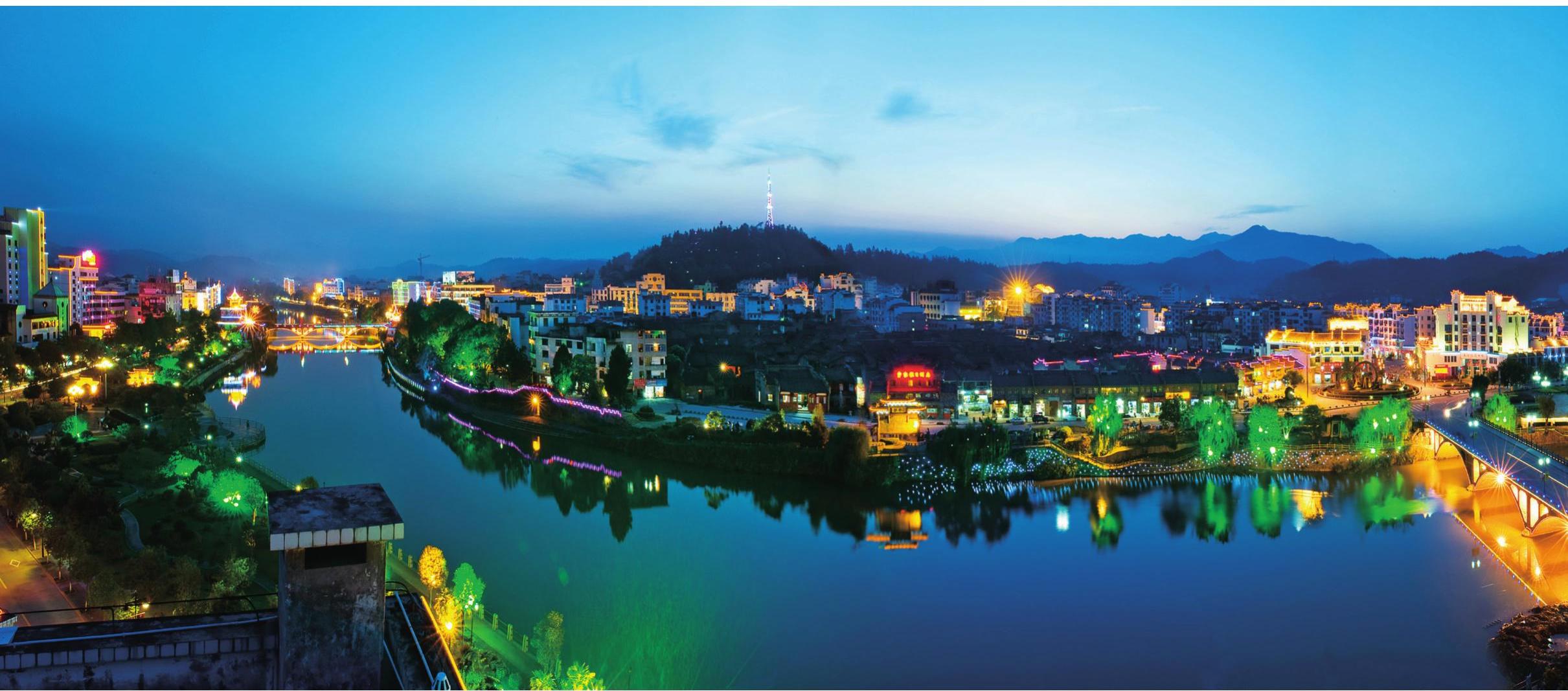
立法宗旨是一部法律的灵魂,对于具体制度的设计起到统领作用。在制定法律时,立法宗旨的确立十分关键。2014年8月通过的预算法修正案,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该法第一条“预算法立法宗旨”进行了修改。
本次《预算法》修改过程中,立法宗旨条款的修改经历了一些波折。修改前的《预算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此处的“国家”表述宏大,其法学意义可以解读为“政府”,那么这条规定显然是将预算作为政府管理社会、上级政府控制下级政府以及政府据以进行自我管理的工具。直至二审稿时,仍未对这一条进行任何修改。在二审稿向社会征求意见时,引发学者们较大议论。一致认为立法宗旨在整部法律中地位重要,如果仍坚持“管理”的定位,整部《预算法》修改所能达到的目标相当有限。2014年4月的三审稿中,对立法宗旨的规定发生根本性变化,该稿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该表述与修改前的表述稍作比对,即可发现其理论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不再强调预算法“管理”、“宏观调控”等方面的作用,而是开宗明义地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作为立论基点,同时对预算制度提出了“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要求,最后通过的新预算法中采纳了此项表述。
每一部法律,必然会被打上其所处时代的烙印。1994年《预算法》通过之时,我国尚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虽然在八十年代时就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计划经济”的色彩尚十分浓厚;这时制定并且开始实施的《预算法》,无可避免地将预算作为国家管理的工具和手段,整部《预算法》呈现出鲜明的“管理法”色彩。表现在立法宗旨上,是对预算分配和监督职能的强调,将《预算法》的重要功能定位为宏观调控工具。
当前,作为《预算法》生存土壤的时代语境同上世纪九十年代可谓天壤之别。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市场功能的推崇,实际上要求《预算法》乃至整个财政法功能向规范公共财产的收支行为回归。《决定》提出:“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是对预算功能定位的调试,即由“政府管理”向“管理政府”转变,相应地,《预算法》也要实现由“管理法”向“控权法”的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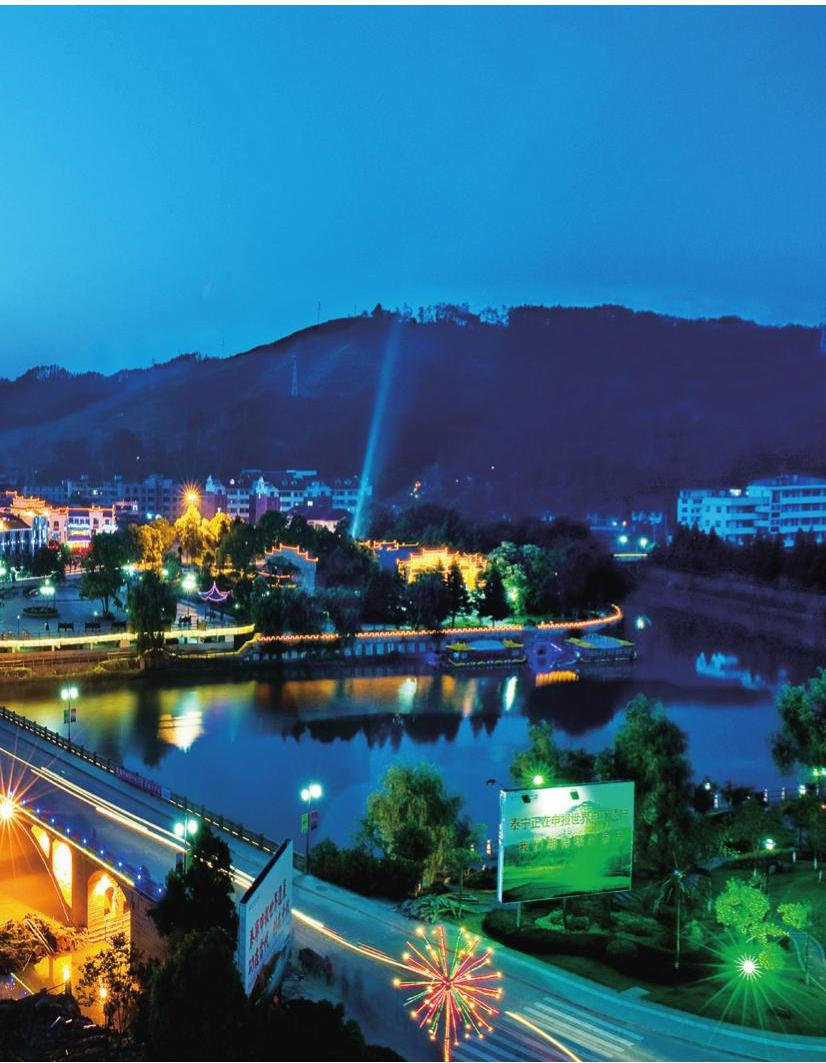
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将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三大战略任务之一,同时直接强调“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由是可见,对于《预算法》功能的认识,已经完成了历史性的“转折”。《预算法》的修改对于立法宗旨作出前述根本性修改,是顺应新的历史形势所作出的战略性调整,意义重大。
立法宗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具体制度的设置,而对《预算法》立法宗旨的修改会直接导致整部法律诸多制度规范的变迁。本次修法实现了预算法由“政府管理的法”向“管理政府的法”的转变,除“立法宗旨”条款外,还有若干体现,包括但不限于:第一,将政府全部收支纳入预算加以规范、监督。新法第4条第2款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第5条则强调:“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并且分别对这“四个账本”进行原则性阐释,初步确立全面管控政府全部收支活动的法律机制。第二,确立并强化预算公开的制度设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现预算活动和预算文本向权力机关和全体纳税人的公开,既能从过程和结果层面实现对政府财政行为的监督,又能通过预算公开的制度性运作,从源头上督促政府在进行财政收支行为时,自觉地合理、合法行事。新法第14条全面规定了预算公开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强调了公开的范围、主体和时间要求,尤其是对社会比较关注的转移支付、举借债务、机关运行经费和政府采购等重点事项,要求特别作出说明或是进行公开。此外,新法第92条对预算公开执行不力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增强了法律规定的约束力。第三,提高人大在预算权配置中的地位,这也是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有力控制。在先前的预算法律制度框架下,人大的预算审批权虚化,很难实质性地管控政府的财政收支,新法增设第22条有关“预算初步审查”的规定,既是增加对政府财政行为的约束,又能通过初步审查意见等向人大代表的印发,便利其实现对政府的预算监督,所以此项制度在“控制政府”意义上,可收“一石二鸟”之功用。第四,尝试改善预算编制粗糙的问题。比如新法第46条要求:“报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的预算草案应当细化。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其功能分类应当编列到项;按其经济性质分类,基本支出应当编列到款。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按其功能分类应当编列到项。”较之过去,在预算编制的细化问题上,本次修法亦有一定进步。
综上所述,对于本次修法在立法宗旨问题上的改进,不能仅从第一条这单一条文出发进行理解,而应该结合整部法律的具体制度展开分析;同时,虽然相关规定仍然存在不足,但立法宗旨的改变是迈出了极有勇气和胆识的一步。又或许是,预算法的一小步,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步。
责任编辑 张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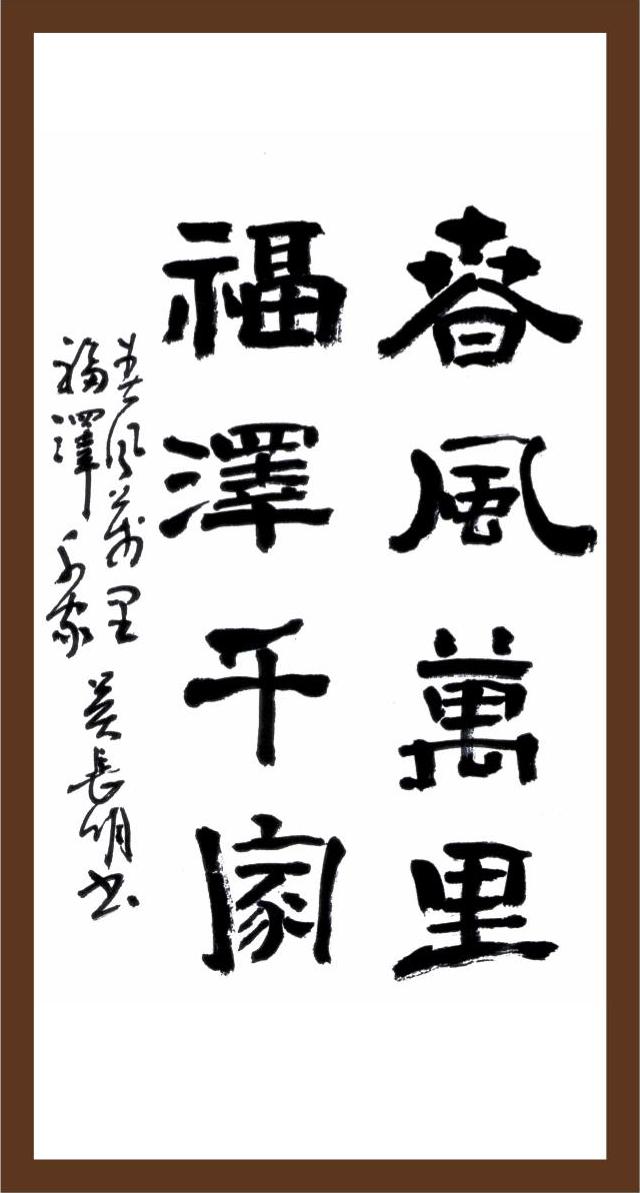
 附件下载:
附件下载:相关推荐
-
无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