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2007年第01期 > 中国财政2007年第01期文章 > 正文
当前位置:首页 > 用户服务 > 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过刊查询 > 《中国财政》2007年第01期 > 中国财政2007年第01期文章 > 正文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的若干法律问题
时间:2020-04-14 作者:刘隆亨
[大]
[中]
[小]
摘要:
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外资税法》)和1994年1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内资税条例》),因税率、列支扣除范围与标准等存在较大差异,引起了政、商、法三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选择了内外资税收双轨制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客观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两法”不仅在内外资企业实际税负、税收优惠、税前列支标准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而且在法律形态上也是不对等的(对“外资企业”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对内资企业用政府“暂行条例”),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税负原则以及WTO公平竞争原则,实行“两法合并”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不仅涉及国家1/3的税收收入,更涉及到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涉及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国有资产的管理,涉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企业的民主法制建设,意义重大。“两法合并”涉及面广,问题比较复杂,有相当的准备工作要做,一定要抓紧、抓好。一不要等,二不要靠,要积极自主地推进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力求做到统一税法、规范税制...
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外资税法》)和1994年1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内资税条例》),因税率、列支扣除范围与标准等存在较大差异,引起了政、商、法三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选择了内外资税收双轨制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客观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两法”不仅在内外资企业实际税负、税收优惠、税前列支标准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而且在法律形态上也是不对等的(对“外资企业”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对内资企业用政府“暂行条例”),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税负原则以及WTO公平竞争原则,实行“两法合并”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不仅涉及国家1/3的税收收入,更涉及到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涉及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国有资产的管理,涉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企业的民主法制建设,意义重大。“两法合并”涉及面广,问题比较复杂,有相当的准备工作要做,一定要抓紧、抓好。一不要等,二不要靠,要积极自主地推进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力求做到统一税法、规范税制、公平税负。改革的具体思路:一是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二是统一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三是统一和规范税前列支扣除标准;四是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体系。
(一)税收管辖权的行使和纳税人的界定。研究和规制企业所得税法所要解决的纳税人范围问题,就要在“两法”现有规定的基础上进行分门别类的归并梳理,同时对新的情况进行法律概括和规制。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确定,按照现有的规定结合国际通行做法,在我国行使税收管辖权时仍然应当采用“注册”地和“住所”地两条标准,即“登记注册地”、“住所”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为中国居民企业法人,否则为中国非居民企业法人。沿用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概念,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准确和便于操作。合乎规范性地行使国家税收管辖权,也是对我国主权行使的具体化。
(二)统一并降低“两法”税率。“两法合并”的核心问题是税率的统一。虽然“两法”名义税率为33%,由于“两法”减免税优惠和税前列支标准项目不同,造成实际税负差别很大。据测算,当前内资企业实际税负为25%左右,“外资企业”实际税负为13%左右,几乎相差一倍。所以,通过“两法合并”要尽快解决企业所得税存在的名义税率偏高、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均的问题,保证内外资企业纳税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我认为,税率的确定,首先要考虑对企业的影响程度,缩小内外资企业之间税负水平的差距,促进企业的发展;其次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对经济发展不同地区的影响,还要考虑企业所得税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及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保持与周边国家税率相当或略低的水平,保持税制的竞争性。因此,比较合理的选择是税率统一由33%降至25%,有增有减,保持税收的稳定与发展。保持25%所得税率不会影响国家财政和企业的承受能力,过高的名义税率反而会造成企业对税收的畏惧心理,产生偷逃税的现象,也易滋生腐败。
(三)规范所得税前的列支扣除标准。现行的“两法”中存在列支扣除项目和标准不明确、不规范的问题。列支扣除直接涉及应纳税所得额税基的大小,与税收优惠从法律上来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税前列支扣除是指企业为取得收入而支付的成本、费用和损失,是企业应当享受的权益,是国家对纳税人权益的让渡,该扣除的不扣除是对纳税人权益的不尊重和侵犯;而税收优惠是在税前列支扣除后进入承担所得税纳税义务领域,即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家给纳税人一种或一定程度的免责规定。税前列支扣除和税收免责优惠虽然都直接影响纳税人的税负,但其过程和法律意义是不同的。因此,在“两法合并”中必须明确规定税前列支扣除所应遵守的原则,包括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相关性原则、确定性和合理性原则。如《内资税条例》对计税工资的限制性规定应当取消,准予工资性支出按实际情况列支扣除,既体现“两法”统一平等,又体现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公益救济性捐赠列支扣除也应取消对内资企业的限制,实现内外统一。
(四)统一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几乎是所有招商引资国家和地区的通常选择。我国现行“两法”中对税收优惠的规定存在不公平、不平等现象,比如《外资税法》30条中就有10条规定是属于税收优惠方面的,优惠种类多、幅度大;《内资税法条例》20条中只有3条是属于税收优惠方面的,优惠面狭窄、幅度小。而且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实际优惠大大超过名义优惠,优惠多、乱、杂,以及越权减免税收屡禁不止等现象,不仅助长了企业的依赖性,减少了国家的税收,而且不透明,易滋生腐败。在“两法合并”过程中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为此,首先在思想观念上要实现三个转变,即由依靠政策的优惠转变到依靠环境的优惠;由依靠资金(让利)的优惠转变到依靠机制(效率)的优惠;由直接优惠为主转变到间接优惠为主。其次,对现有的各种优惠进行清理和完善。该取消的必须取消,比如取消《内资税条例》对校办企业、劳务企业税收优惠措施,沿海地区的优惠也可考虑逐渐取缔;该修订的应尽快修订,比如应当统一明确加速折旧,按照产业政策导向和发展序列要求,对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和通讯业、农林水利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不分区域都应给予优惠政策;该保留的必须保留,并要落实,比如环保产业优惠、高新技术产业优惠、西部开发优惠,以体现新的产业政策和保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该增加的必须增加,比如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再就业、投资基金市场等金融部门的发展,税收优惠必须增加新的规定;对不确定的税收优惠需要灵活掌握的应灵活规定,有的可以采取控制总量,有的可以采取财政补贴,有的可以采取过渡期。总之,要规范享受优惠的资格和优惠的执行程序,形成科学的优惠体系,并且加强管理。还要注意与税前列支扣除相衔接,不要相互抵触、相互矛盾。要注意优惠政策的时间性、效益性,使我国税收优惠进入良性循环。
(五)与个人所得税的衔接问题。由于对所得征税的复杂性和按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划分纳税的局限性,为了避免重复课税和防止税收空隙与流失,必须注意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法的衔接。这种衔接着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企”、“个”两税征收范围和减免项目边缘的衔接;二是“企”、“个”两税税率和扣除项目边缘的衔接,否则会造成对纳税人的税负不公。在“企”、“个”两税征收范围上,对个人、家庭等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只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企”、“个”两税税率的衔接上,现在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分别为25%左右和11%左右,如果企业所得税按25%的比例税率征税,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也要与此相适应,应把偏高的个人所得税率适当降下来;在“企”、“个”两税税收减免与扣除项目上,不能相互抵触、冲突,要和谐一致,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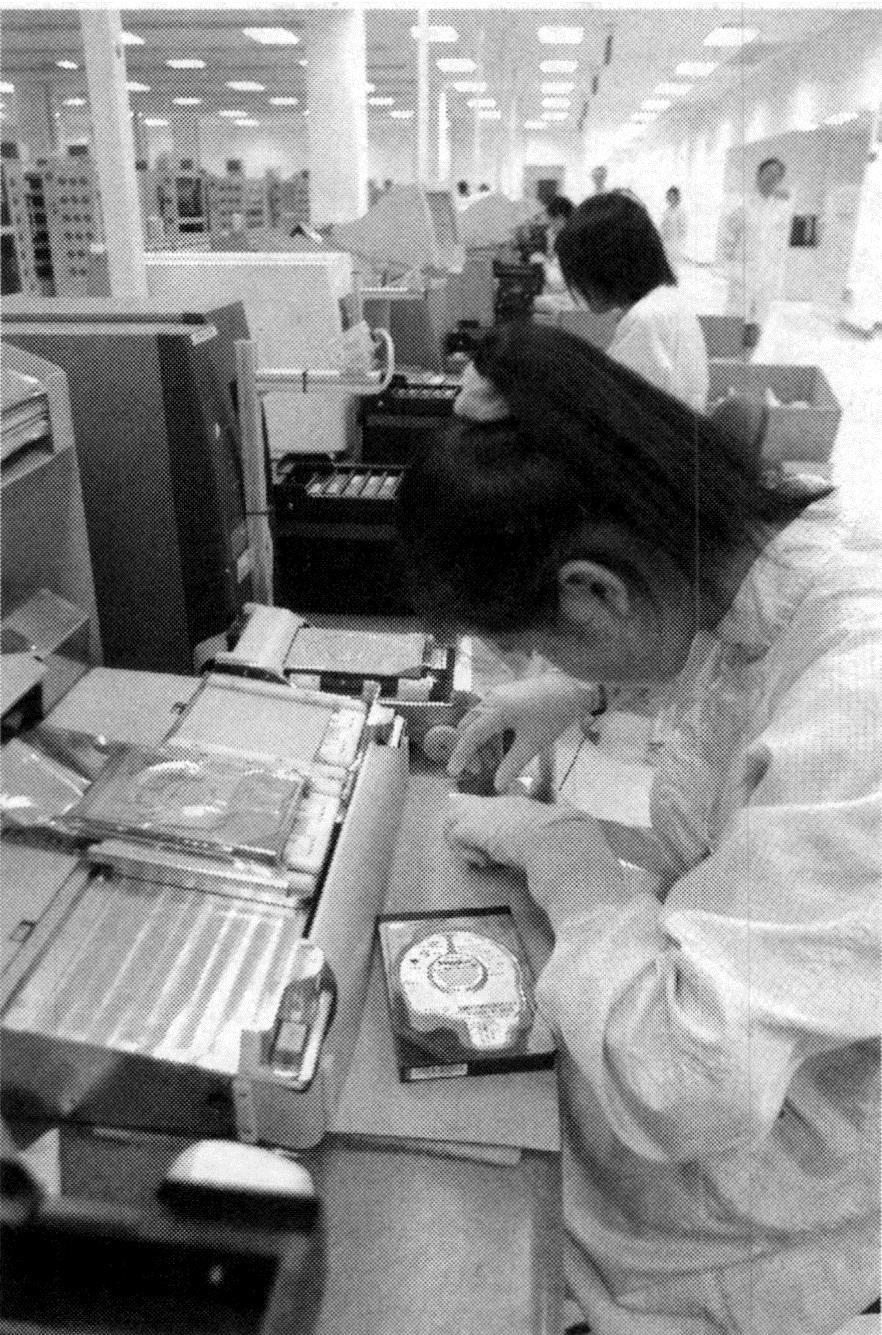
(六)股息性所得的处理。股息性所得又称资本利得。对资本利得,我认为应征收企业法人所得税。因为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以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为纳税原则,除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开征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我国也应当逐步开征。对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应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个人资本利得,目前应暂缓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必须抓紧创造条件准备开征。因为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对于股票实行的是一年一免的政策,现在开征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时机尚未完全成熟。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 李颖
 附件下载:
附件下载:相关推荐
-
无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邮编:100036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40014 投诉举报电话:010-88227120
京ICP备1904795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投约稿系统升级改造公告
各位用户:
为带给您更好使用体验,近期我们将对投约稿系统进行整体升级改造,在此期间投约稿系统暂停访问,您可直接投至编辑部如下邮箱。
中国财政:csf187@263.net,联系电话:010-88227058
财务与会计:cwykj187@126.com,联系电话:010-88227071
财务研究:cwyj187@126.com,联系电话:010-88227072
技术服务电话:010-88227120
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财政杂志社
2023年11月
-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 投诉举报电话:010-88227120
- 邮编:100036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





